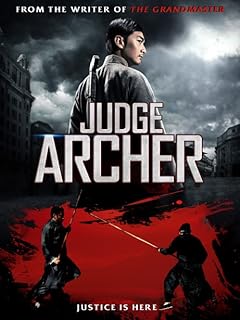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6-05-13 08:45:48
柳白猿與徐浩峰:觀察者眼中的武林和世界
在中國大陸導演中,似乎還沒有誰有徐浩峰那樣對中國傳統文化精深而全面的了解。和他面對面的聊天,除了電影之外,他還可以把中國古典繪畫、書法和文學的基本原理與要素講解的頭頭是道。
在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之前,徐浩峰在中央美院附中學畫,師從國畫名家許仁龍老師。與我們通常對國畫寫意花鳥山水恣意縱橫一氣呵成的觀感理解相反,徐浩峰從許老師那裡繼承的觀念是,國畫是一種細緻和理性的藝術。磅礴的氣勢,揮灑自如的筆觸和留白意境深遠的構圖其實都是反覆思考掂量和縝密構圖後的產物。用徐浩峰的話說,這是一種「經營位置」的結果。而所謂的「下筆有神一揮而就」只是對中國傳統視覺藝術一種誤解式想像。
與此同時,徐浩峰還在習武。中國文化的標誌性特徵之一就是它貫穿所有領域的聯通性:存在於國畫中的原理,在武學中也潛移默化地成為其內在運行邏輯。例如,徐浩峰在解釋詠春原理時強調這是一種刺客拳,是特意為身形瘦小力薄體弱的人所設計的技擊技巧——在行刺的時候身高體壯的人很容易引人矚目,往往還未行動就已經被人控制住了;因而與講究力量和勇猛氣勢的西方拳術相區別,詠春更多地是通過理性思考去把握自身所處的位置,去預判對手的動作,依靠比敵手更敏捷的反應和更豐富的行動經驗而搶佔上風。
無論是繪畫還是武術,在徐浩峰的觀念中,都是理性、細緻和對自身位置的「經營」。這樣與流行觀念大相逕庭的視野,是塑造徐浩峰電影特點的源頭。
從2013年由徐浩峰擔任編劇的《一代宗師》中,觀眾開始感受到一股和通常功夫片不太一樣的氣息。如果說葉偉信執導的《葉問》系列依然停留在內涵粗線條的視覺表現性功夫層次,那麼《一代宗師》中的葉問則向觀眾傳達出了與眾不同的對武術本身的認知:影片著迷於對於武術一招一式所代表的內涵以及對不同門派風格的貫通式理解,而隨後更由招法延伸出對於個人情感命運的哲學化詮釋。影片中的葉問與其說是一代武術家,倒不如說是一位以武術而深人人生的觀察者,一生執著於以武術的原理去參透外在世界的運作原則。看似以電影表現武術,但實則以武術類比人生,它構成了徐浩峰電影創作的一個基本點。
以這個角度看徐浩峰的三部電影作品,《箭士柳白猿》在其中無疑是最極端的一部。如果說《倭寇的蹤跡》和《師父》都或多或少地將武術嫁接於一個具體的故事之上,那麼《柳白猿》則在電影「去情節化」的道路上走的最遠:它有著極度碎片化的敘事、幾乎不能連貫的故事情節和大量隱含著省略和隱喻的表達,這讓習慣於短平快直白表述的中國觀眾很難在九十分鐘內抓住影片的主題所在。從商業片的角度來看,一部以「打」為主的片子建築在走位如此飄忽的敘事平台上是極為挑戰性的嘗試。但與此同時,在「武術」的外殼下,徐浩峰所展示的是一個軍閥政治、武林江湖和個人情感相交織的紛繁複雜時代。柳白猿做為權威的比武仲裁者,所看到的不僅僅是拳腳功夫上的成敗勝負,而更是在不同舞台上進退較力的社會群體。片中的人們行走江湖,或張揚跋扈或隱姓埋名,或野心勃勃或低調隱退,無不代表著一套獨到而又自成體系的人生哲學。這些人生價值觀的衝突對撞,盡收於柳白猿眼中,令他成為一名穿越時間看盡人間悲歡成敗的觀察者。柳白猿的位置,大概也正是徐浩峰自己所期待的理想人生位置:只有通過對世間萬物耐心而細緻的觀察、判斷與思考,他才能在「位置」的經營上佔得永遠的先機。
也正是從這樣的創作初衷出發,《柳白猿》成為了一部可以改寫中國式動作電影風格的破格之作。精心設計的打鬥、讓人眼花繚亂的冷兵器展示和錯綜複雜的武行與政治之間的糾葛實際上都成了包裹在飄飛的思維情緒之外的「殼」。人物冷峻、乖張和跳躍的行為話語邏輯將其托至了某種「精神」與「肉體」分離而「不在場」的古怪狀態。武打動作成為了思緒飄飛而「在別處」的證據,它所形成的「詩意」賦予了影片極強的文學作者化思辨意識。徐浩峰意在推翻影像對功夫的單一呈現模式,將武術動作從單純的視覺展現中解放出來,賦予其精神、情感和道德判斷上的多重涵義,將其由動作引向思索,由娛樂轉化為藝術,使其成為情感和意義表達的載體。
在徐浩峰之前,幾乎所有功夫電影的劇情核心都是建立在正邪鬥爭的二元對立意識形態上的,後者的粗放直接和簡單通俗使影片中的動作具有為觀眾可以輕易理解的文本意義,而主要人物在道德上的正面形象同樣也是動作可以達到情緒力度表現高潮的有力助推器。而在《柳白猿》中,這正義與邪惡的對峙則幾乎消失了。柳白猿面臨的是自己做為仲裁者的使命與不斷糾葛翻滾的個人情感之間的內在衝突,一切善惡對錯都消解在瞬間取捨中被徹底改變的無常的命運,他所躊躇而不能決定的,並不是對正邪的判斷,而是對意義的終極拷問。這成了武林世界中功夫較量的核心推動力。
徐浩峰在訪談中認為中國武打片做為一個類型其實是京劇藝術在螢幕上的最後綻放。如此看來,《箭士柳白猿》大概繼承了京劇美學核心中最重要的一點:以動作為本體的形式永遠在為動作之外飄散於空中的意境塑造而服務。普通功夫電影中大幅度的身體動作、迅如疾風的動作頻率和重壓泰山式的出招力度在《柳白猿》中都被完全放棄。他寧可犧牲動作的觀賞性,而只為展示傳統武術動作的韻律。在這背後包含著徐浩峰的核心武觀:武術不是人們頭腦中華麗炫目的張揚想像,相反它是充滿精神思辨性的身體真實。在傳統功夫電影中被奉為核心而展現的動作,在《柳白猿》中成為了襯託人物精神活動的外延,承擔起了塑造他們獨特個性的最主要責任。
如果說在功夫片發展歷史上,關於它是否具有藝術性的爭論最後都幾乎以否定而告終。那《柳白猿》終於讓我們隱約地看到了功夫片某種以動作為載體而呈現作者化精神主體的嶄新可能性。而這種對於功夫電影從內容到形式上的更新,都離不開徐浩峰本人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精神紋理的內在展示意圖。他借用了柳白猿的視角,對那個幾乎已經消逝的中國文化精神的主體世界投去充滿情感和懷念的一瞥,在觀察中呈現出遊走其中的最佳「位置」感。這是《箭士柳白猿》之於徐浩峰思想的最大價值所在。
在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之前,徐浩峰在中央美院附中學畫,師從國畫名家許仁龍老師。與我們通常對國畫寫意花鳥山水恣意縱橫一氣呵成的觀感理解相反,徐浩峰從許老師那裡繼承的觀念是,國畫是一種細緻和理性的藝術。磅礴的氣勢,揮灑自如的筆觸和留白意境深遠的構圖其實都是反覆思考掂量和縝密構圖後的產物。用徐浩峰的話說,這是一種「經營位置」的結果。而所謂的「下筆有神一揮而就」只是對中國傳統視覺藝術一種誤解式想像。
與此同時,徐浩峰還在習武。中國文化的標誌性特徵之一就是它貫穿所有領域的聯通性:存在於國畫中的原理,在武學中也潛移默化地成為其內在運行邏輯。例如,徐浩峰在解釋詠春原理時強調這是一種刺客拳,是特意為身形瘦小力薄體弱的人所設計的技擊技巧——在行刺的時候身高體壯的人很容易引人矚目,往往還未行動就已經被人控制住了;因而與講究力量和勇猛氣勢的西方拳術相區別,詠春更多地是通過理性思考去把握自身所處的位置,去預判對手的動作,依靠比敵手更敏捷的反應和更豐富的行動經驗而搶佔上風。
無論是繪畫還是武術,在徐浩峰的觀念中,都是理性、細緻和對自身位置的「經營」。這樣與流行觀念大相逕庭的視野,是塑造徐浩峰電影特點的源頭。
從2013年由徐浩峰擔任編劇的《一代宗師》中,觀眾開始感受到一股和通常功夫片不太一樣的氣息。如果說葉偉信執導的《葉問》系列依然停留在內涵粗線條的視覺表現性功夫層次,那麼《一代宗師》中的葉問則向觀眾傳達出了與眾不同的對武術本身的認知:影片著迷於對於武術一招一式所代表的內涵以及對不同門派風格的貫通式理解,而隨後更由招法延伸出對於個人情感命運的哲學化詮釋。影片中的葉問與其說是一代武術家,倒不如說是一位以武術而深人人生的觀察者,一生執著於以武術的原理去參透外在世界的運作原則。看似以電影表現武術,但實則以武術類比人生,它構成了徐浩峰電影創作的一個基本點。
以這個角度看徐浩峰的三部電影作品,《箭士柳白猿》在其中無疑是最極端的一部。如果說《倭寇的蹤跡》和《師父》都或多或少地將武術嫁接於一個具體的故事之上,那麼《柳白猿》則在電影「去情節化」的道路上走的最遠:它有著極度碎片化的敘事、幾乎不能連貫的故事情節和大量隱含著省略和隱喻的表達,這讓習慣於短平快直白表述的中國觀眾很難在九十分鐘內抓住影片的主題所在。從商業片的角度來看,一部以「打」為主的片子建築在走位如此飄忽的敘事平台上是極為挑戰性的嘗試。但與此同時,在「武術」的外殼下,徐浩峰所展示的是一個軍閥政治、武林江湖和個人情感相交織的紛繁複雜時代。柳白猿做為權威的比武仲裁者,所看到的不僅僅是拳腳功夫上的成敗勝負,而更是在不同舞台上進退較力的社會群體。片中的人們行走江湖,或張揚跋扈或隱姓埋名,或野心勃勃或低調隱退,無不代表著一套獨到而又自成體系的人生哲學。這些人生價值觀的衝突對撞,盡收於柳白猿眼中,令他成為一名穿越時間看盡人間悲歡成敗的觀察者。柳白猿的位置,大概也正是徐浩峰自己所期待的理想人生位置:只有通過對世間萬物耐心而細緻的觀察、判斷與思考,他才能在「位置」的經營上佔得永遠的先機。
也正是從這樣的創作初衷出發,《柳白猿》成為了一部可以改寫中國式動作電影風格的破格之作。精心設計的打鬥、讓人眼花繚亂的冷兵器展示和錯綜複雜的武行與政治之間的糾葛實際上都成了包裹在飄飛的思維情緒之外的「殼」。人物冷峻、乖張和跳躍的行為話語邏輯將其托至了某種「精神」與「肉體」分離而「不在場」的古怪狀態。武打動作成為了思緒飄飛而「在別處」的證據,它所形成的「詩意」賦予了影片極強的文學作者化思辨意識。徐浩峰意在推翻影像對功夫的單一呈現模式,將武術動作從單純的視覺展現中解放出來,賦予其精神、情感和道德判斷上的多重涵義,將其由動作引向思索,由娛樂轉化為藝術,使其成為情感和意義表達的載體。
在徐浩峰之前,幾乎所有功夫電影的劇情核心都是建立在正邪鬥爭的二元對立意識形態上的,後者的粗放直接和簡單通俗使影片中的動作具有為觀眾可以輕易理解的文本意義,而主要人物在道德上的正面形象同樣也是動作可以達到情緒力度表現高潮的有力助推器。而在《柳白猿》中,這正義與邪惡的對峙則幾乎消失了。柳白猿面臨的是自己做為仲裁者的使命與不斷糾葛翻滾的個人情感之間的內在衝突,一切善惡對錯都消解在瞬間取捨中被徹底改變的無常的命運,他所躊躇而不能決定的,並不是對正邪的判斷,而是對意義的終極拷問。這成了武林世界中功夫較量的核心推動力。
徐浩峰在訪談中認為中國武打片做為一個類型其實是京劇藝術在螢幕上的最後綻放。如此看來,《箭士柳白猿》大概繼承了京劇美學核心中最重要的一點:以動作為本體的形式永遠在為動作之外飄散於空中的意境塑造而服務。普通功夫電影中大幅度的身體動作、迅如疾風的動作頻率和重壓泰山式的出招力度在《柳白猿》中都被完全放棄。他寧可犧牲動作的觀賞性,而只為展示傳統武術動作的韻律。在這背後包含著徐浩峰的核心武觀:武術不是人們頭腦中華麗炫目的張揚想像,相反它是充滿精神思辨性的身體真實。在傳統功夫電影中被奉為核心而展現的動作,在《柳白猿》中成為了襯託人物精神活動的外延,承擔起了塑造他們獨特個性的最主要責任。
如果說在功夫片發展歷史上,關於它是否具有藝術性的爭論最後都幾乎以否定而告終。那《柳白猿》終於讓我們隱約地看到了功夫片某種以動作為載體而呈現作者化精神主體的嶄新可能性。而這種對於功夫電影從內容到形式上的更新,都離不開徐浩峰本人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精神紋理的內在展示意圖。他借用了柳白猿的視角,對那個幾乎已經消逝的中國文化精神的主體世界投去充滿情感和懷念的一瞥,在觀察中呈現出遊走其中的最佳「位置」感。這是《箭士柳白猿》之於徐浩峰思想的最大價值所在。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