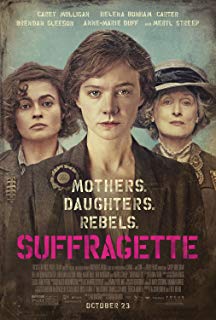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6-03-04 23:05:07
誰似浮雲知進退
我們對有一些片子十分寬容,可以輕易打出四星或以上,另一些卻用全然不同的苛刻標準來衡量。其實也很好理解,無論是超級英雄片、科幻片或是驚悚片,它們離我們的生活相對遙遠,觀眾有意無意地會將自己抽離在外,於是可以用隔岸觀火的心態去窺視;
而現實主義劇情片則不同,它其中描繪的場景與每天會發生在身邊的事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既視感強烈」會產生兩個指向,其一是引起部份觀眾的情感共鳴,往往與影片所希望表達的主旨一致,產生積極效用。但由於個體差異,其二則是引起另外一些觀眾的情緒反彈。當然,我們舉例子的時候不能身邊即世界,但是觀影感受終究是私人的,代入感越強,對細節偏差的容忍度就越低,打個不恰當地比方就是會產生恐怖谷效應,放在這個片子裡——或當今社會語境之下,很容易想見究竟是哪些人在鼓吹「女性地位已空前提高」——即是:
電影本身沒有足夠強烈或直接的事件衝突推動女主的角色轉變,使得故事本身缺乏說服力;或者針對現在女權主義者的「叫囂」,指出男女本來就有別,有些工作本來就不適合女性做,要求平等不是有病麼;我自己/我身邊的女性待遇都不錯,並沒有感受到很多性別歧視,當時女性地位低下沒錯,既然現在已提升又何必日日重提事事計較,諸如此類。
近年總有一些詞出現頻率忽然變得很高,從而使詞義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女權,情懷,直男,這些詞後面被加上「癌」,徹底妖魔化,很多人說著它們的同時,根本不懂得也無心考慮這些詞彙的初始語境和它們究竟意味著什麼,只是大家都在用於是就跟著用了。詞義一旦擴大,人們的敏感性便隨之降低,比如那些自稱「寶寶」的愚蠢——啊不對這個例子不對,這些傻X還是很噁心,該拉黑的千萬別手軟。
語言的濫用對拉低大多數路人的普遍觀感可謂推波助瀾,對一個不甚了解、無喜無怒的事物,「弱勢群體」在路人原是一個加分項,卻因為非正常的刷關注造成別人根本無心去關注孰是孰非,只想把女權和反女權全部叉出去,這實在怨不得別人。
我個人對國內的民間女權(可算是民間科學的對應詞吧)也實在沒什麼好感,因為其中參雜著太多政治正確,和太多掛羊頭賣狗肉。觀看這部影片的同時也有類似的顧慮:電影本身所持的立場是什麼?拍片是為了陳述觀點還是炒作熱點賣錢?畢竟現在錢好賺了嘛,有些電影目的也難說純粹,當有可惡的新娘這種打著某種名義干另一種事情的影片出現,我們再也不能說電視圈的拍電影只是為了圈錢了,圈錢不可怕,不但圈錢而且夾帶私貨還有腦殘粉主動當槍,這種把什麼情懷夢想以及更多掰扯不清的事情放在一起,從不跟你講邏輯只講主觀感受的人一旦出現,就再沒有什麼爭論的必要了。
好在這部影片本身足夠誠懇。當然,它有很多不足,但有一點極其真切地打動了我,這個等下後面說,個人認為這點足以遮蓋所有不足,所以我給了五星。
其實影片中已經表現得清楚明白了,想要獲得弱勢群體之外人群的注意十分困難,而就在弱勢群體內部很多人也會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不願去改變現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得不償失」。她們有自己的社交圈、圈中(無論是誰在引導)有主導輿論、有丈夫與孩子,或有苦衷無法發聲,為了一些很難說到底能不能爭取到、能爭取到多少的權利實在不值得承擔失去一切的風險。
前面說到打動我的一點是,你的面前從來都有選擇,而你要選擇自己會做什麼。當然,真正經歷了歧視的人更「容易」覺醒,但也並不意味著女主的動機不夠充分,畢竟世界上還有那麼多LGBT友好人士。關鍵是你要明白,自己為什麼發聲與如何發聲。
我原先也是個身邊即世界派,因為沒有真切體會過因性別帶來的權利缺失,也就從未為了平權去做出過什麼事情,即使我自己也是性少數人群中的一員。作為一個社恐症,縮幾乎是一種本能,另一方面我一直以來的想法是愛情就是愛情,它不因LGBT與否而變得偉大或渺小。換言之,電影就是電影本身,底線是不性別歧視,但也不用刻意顯得政治正確而安插非必要性的場景、台詞乃至角色。
(尤其是近年來無論LGBT還是女權在某些人那裡一如既往受到歧視不說,在另一些人眼裡卻儼然成了某種身份標識,同性戀「反而」高人一等了,咄咄怪事——這麼說的意思是,反歧視最重要的一點是去特殊化,無論是用以標榜或用以嘲諷都在廣義上使之分離於另一群體,這很不正常。當然不僅指影視劇賣腐。圈粉小鬥士同樣可怕。)
這部片子中的女性為了爭取權利而從事暴力活動,同志亦凡人中近乎濫交的誇張鏡頭描寫,這是否一種矯枉過正,它們真的有必要嗎?賽佛·哈定說,武力是無能者最後的手段,在這裡也同樣適用嗎?
首先要推翻我原本的想法,站在電影創作的角度,去特殊化仍然很重要,站在電影創作者的角度——總有人要站出來做這件事——「誇張」必不可少。我們需要為正當一種權利而吶喊,因為藉助影像媒介發聲這件事是結果導向的,通過哪一個環節、哪一種方式抓取觀眾的注意力不重要,最終抓取了觀眾的注意力,並令人們有所思考比較重要。所有讓人覺得如鯁在喉、不符合現世道德邏輯準則的事情,都是為了確保觀眾能夠理解一個弱勢群體的苦衷:如果不這樣誇張地把這些指出來,觀眾就不會意識到,從而理解和接受。
在電影設定中當時的情況下,暴力是否唯一的解決方法我不知道,但的確是這些婦女所能想出的最優方案,也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傷亡最小並逐步達成期望的結果。暴力從來不是必須的,但是絕不能因為不希望使用暴力,對方以暴力相待時就不去還手。
這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啊。有些公司/導演的片子爛成一灘仍然有無數熱情粉絲高呼好好好買買買,另一些同類型、水準甚而更高的作品,卻遭到或許是同一批觀眾幾乎零容忍度的攻擊,究竟岔在了哪裡可能只能歸結於微妙的氣質,不過這也正是開頭第一段所說,現實主義作品是有門檻的。
是偶然跟人說著別的,想起了這部片子,我之前看的時候其實有些不認同,但今天順口就用了其中一個觀點,想了想竟然無法反駁自己。
我不是什麼女權主義者,甚至不是個人權主義者,原來對人類的未來看法很悲觀的。往大里說萬物興衰有本,人類無論破壞或保護自然、戰爭或保持和平最終都會自行滅絕;往小里說人各有命,活好自己的一世已然不易,連死後會去往哪裡都還不知道,何苦操心太抽象的「人權」?不過寫著寫著我感覺又把自己說服了。以後儘量成為一個有用的人,為該死的人類做點好事吧。
另外關於男女有別那條,說得沒錯,女性去從事更男性化的職業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生理代價,所以有時候我們不提倡女性做出不利於自己的選擇,這是出於社會資源分配的考量,也意在避免女性受到不必要的傷害;但如果後果被申明的前提下,一位女性仍然決定自己可以去和男性做平等競爭,就證明她已經意識到並認可自己將要承擔的風險,這時候選擇和從事職業是她的權利與自由。
最後,不管你是哪個性別,請反思自己的說話習慣吧,帶有歧視性的群體詞彙儘量少用,我也會儘量少說某一類型的人是狗屎的。就像所有正派人被問及「他們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回去?」時說的:至少我們不能跟他們一樣啊。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