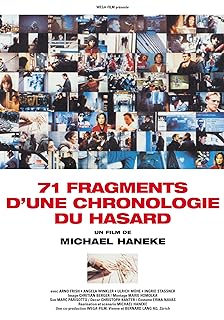電影訊息
禍然率71--71 Fragments
編劇: 麥可漢內克
演員: Gabriel Cosmin Urdes Lukas Miko Otto Grunmandl Anne Bennent Udo Samel
机遇编年史的71块碎片/机缘七十一面体/冰川三部曲之三:机遇编年史的71块碎片
導演: 麥可漢內克編劇: 麥可漢內克
演員: Gabriel Cosmin Urdes Lukas Miko Otto Grunmandl Anne Bennent Udo Samel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5-07-27 04:45:55
如果描述美麗,它立刻就變成謊言
局部的看見
在《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中,麥可·哈內克選擇將「暴力」作為他影像冰川的一角,以此痛擊觀眾,從而牽引出「世界是由碎片構成的」這一現實問題。
由一個連續事件所關聯的人,因為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在場而看見事件不同的局部資訊,再由於各自認知方式、情感方式的不同而得出差異判斷——這種「局部的看見」打碎了連續事件及其真實。
實際上「連續事件」只是人的一廂情願,我們習慣以「很久以前」和「從此以後」切斷事件遙不可及的初始和結局,從而廓出一個故事,也唯有這樣,故事才能被有始有終地說完,無論是童話、偵探故事還是新聞報導。
兒時生活中,父親的缺席,也許是造成麥可·哈內克認識世界不完整和破碎的重要原因,他自己的婚姻也在重複著碎片模式[1]。哈內克對這樣的世界深感不安並且深信不疑,所以才會有《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這樣的電影,以碎片敘事描述碎片世界:整部電影由互不相識的人的生活片段拼接而成,如果沒有結尾的槍殺事件,他們也許永遠都不會有什麼交集。
並且電影著力描述的,是另一種更深的碎片化:人與人的缺乏溝通。流浪少年因為語言不通而無法與人溝通、父女間因為生活關聯冷淡而沒有溝通、中年夫婦與收養的孩子無法溝通……馬可·米蘭與同學、加油站司機、銀行、路人等所有人都無法溝通,即便與母親在通電話,看上去他開心地說了很多,但沒有一次是表述他真實的處境和煩惱的,「我們滔滔不絕地說,但沒有交流,越親密溝通越差,我們越親近,越少交談」[2]。
整個世界是一座巴比倫塔。
松潰的復原
哈內克通過一部電影,想復原的並不是這個真實案件的來龍去脈。他認為「電影總是假裝描繪的是整體」[2]是可疑的,全知視角自始至終就脫離真實,藝術對真實的復原,如果僅為了滿足觀眾對了解事件的需求,便可能淪為模仿秀。從這個意義上說,哈內克的《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比格斯·范·桑特的《大象》走得更深、更貼近真實。
電影以電視新聞畫面開始、以重複的新聞畫面結束——哈內克不滿於新聞報導的偽真實的面目,在它滔滔不絕的偽交流(人和電視不存在交流,通過電視短逝的語言了解事件真相是不可能的)的語言中撕開一個裂口,插入一部電影來描述他認為的世界真實的樣貌。
將戰爭時事、街頭槍殺案、聖誕節時俗、娛樂新聞(麥可·傑克遜的孌童事件)打包在一起,通過電視螢幕扔給觀眾——哈內克對這種媚俗至極的謊言播報感到厭惡。他有更好的語言來敘述,他認識到觀眾的自身經歷必將導致不同的理解方式,並誠實地尊重這一現實,「洩漏一些碎片」、「給觀眾擴大理解的可能」。
他尋找並展示事件中更多的關聯性,越多的線索,越能更好地拼湊現實。但在這裡需要克制,要克服「在電影的主流,我們總是假裝無所不知」[2]的習慣,只能提供有限的、松潰的復原材料,作者不可逾越現實、完成唯一的敘述,應給觀眾足夠的空餘和留白。從這個意義上說,哈內克的《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比蓋·里奇《兩桿大煙槍》更冷靜、更真實——他拒絕了危險的娛樂性和戲劇性。
碎片,仍是碎片
電影23分鐘處有一個打桌球的長鏡頭,哈內克給我們留了3分鐘的時間,去觀看這個瑣細的場景,這已經突破了大多數觀眾的底線。對於馬可·米蘭來說,他的積怒和爆發正是由這無數的3分鐘完成的。3分鐘會讓我們經歷「明白—有趣—厭倦—憤怒—冷靜—接受—理解」這一完整過程,但前提是你沒有從中間以快進替換其後的體驗機會。這個長鏡頭是在真實、同時上顯示力量的一個範例,如果你能接受,電影中還有一個接電話的固定長鏡頭(8分鐘)值得反覆體會。
是的,這鏡頭真實,僅僅是真實,而不是美。哈內克認為「描畫或者嘗試描畫美麗,它馬上就會變成謊言」[2],他只展示真相,而能否發現真相後面的美,則是觀眾的課題。
孤獨、隔離、失望、出逃、憤怒、笑、憂鬱、失神、厭倦……每一個人物都是一塊碎片,每一刻的情感都是一塊碎片,能在這71塊碎片中,還原出怎樣一部生活編年史——與哈內克已無多大關係,只與你自己有關。
[1]麥可·哈內克的父親在其三歲時離家,直到成年,他才與父親相會。麥可·哈內克與前任妻子生育一個孩子,二任妻子為他帶來的三個繼子。
[2]摘自金魚J整理的哈內克訪談。
在《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中,麥可·哈內克選擇將「暴力」作為他影像冰川的一角,以此痛擊觀眾,從而牽引出「世界是由碎片構成的」這一現實問題。
由一個連續事件所關聯的人,因為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在場而看見事件不同的局部資訊,再由於各自認知方式、情感方式的不同而得出差異判斷——這種「局部的看見」打碎了連續事件及其真實。
實際上「連續事件」只是人的一廂情願,我們習慣以「很久以前」和「從此以後」切斷事件遙不可及的初始和結局,從而廓出一個故事,也唯有這樣,故事才能被有始有終地說完,無論是童話、偵探故事還是新聞報導。
兒時生活中,父親的缺席,也許是造成麥可·哈內克認識世界不完整和破碎的重要原因,他自己的婚姻也在重複著碎片模式[1]。哈內克對這樣的世界深感不安並且深信不疑,所以才會有《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這樣的電影,以碎片敘事描述碎片世界:整部電影由互不相識的人的生活片段拼接而成,如果沒有結尾的槍殺事件,他們也許永遠都不會有什麼交集。
並且電影著力描述的,是另一種更深的碎片化:人與人的缺乏溝通。流浪少年因為語言不通而無法與人溝通、父女間因為生活關聯冷淡而沒有溝通、中年夫婦與收養的孩子無法溝通……馬可·米蘭與同學、加油站司機、銀行、路人等所有人都無法溝通,即便與母親在通電話,看上去他開心地說了很多,但沒有一次是表述他真實的處境和煩惱的,「我們滔滔不絕地說,但沒有交流,越親密溝通越差,我們越親近,越少交談」[2]。
整個世界是一座巴比倫塔。
松潰的復原
哈內克通過一部電影,想復原的並不是這個真實案件的來龍去脈。他認為「電影總是假裝描繪的是整體」[2]是可疑的,全知視角自始至終就脫離真實,藝術對真實的復原,如果僅為了滿足觀眾對了解事件的需求,便可能淪為模仿秀。從這個意義上說,哈內克的《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比格斯·范·桑特的《大象》走得更深、更貼近真實。
電影以電視新聞畫面開始、以重複的新聞畫面結束——哈內克不滿於新聞報導的偽真實的面目,在它滔滔不絕的偽交流(人和電視不存在交流,通過電視短逝的語言了解事件真相是不可能的)的語言中撕開一個裂口,插入一部電影來描述他認為的世界真實的樣貌。
將戰爭時事、街頭槍殺案、聖誕節時俗、娛樂新聞(麥可·傑克遜的孌童事件)打包在一起,通過電視螢幕扔給觀眾——哈內克對這種媚俗至極的謊言播報感到厭惡。他有更好的語言來敘述,他認識到觀眾的自身經歷必將導致不同的理解方式,並誠實地尊重這一現實,「洩漏一些碎片」、「給觀眾擴大理解的可能」。
他尋找並展示事件中更多的關聯性,越多的線索,越能更好地拼湊現實。但在這裡需要克制,要克服「在電影的主流,我們總是假裝無所不知」[2]的習慣,只能提供有限的、松潰的復原材料,作者不可逾越現實、完成唯一的敘述,應給觀眾足夠的空餘和留白。從這個意義上說,哈內克的《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比蓋·里奇《兩桿大煙槍》更冷靜、更真實——他拒絕了危險的娛樂性和戲劇性。
碎片,仍是碎片
電影23分鐘處有一個打桌球的長鏡頭,哈內克給我們留了3分鐘的時間,去觀看這個瑣細的場景,這已經突破了大多數觀眾的底線。對於馬可·米蘭來說,他的積怒和爆發正是由這無數的3分鐘完成的。3分鐘會讓我們經歷「明白—有趣—厭倦—憤怒—冷靜—接受—理解」這一完整過程,但前提是你沒有從中間以快進替換其後的體驗機會。這個長鏡頭是在真實、同時上顯示力量的一個範例,如果你能接受,電影中還有一個接電話的固定長鏡頭(8分鐘)值得反覆體會。
是的,這鏡頭真實,僅僅是真實,而不是美。哈內克認為「描畫或者嘗試描畫美麗,它馬上就會變成謊言」[2],他只展示真相,而能否發現真相後面的美,則是觀眾的課題。
孤獨、隔離、失望、出逃、憤怒、笑、憂鬱、失神、厭倦……每一個人物都是一塊碎片,每一刻的情感都是一塊碎片,能在這71塊碎片中,還原出怎樣一部生活編年史——與哈內克已無多大關係,只與你自己有關。
[1]麥可·哈內克的父親在其三歲時離家,直到成年,他才與父親相會。麥可·哈內克與前任妻子生育一個孩子,二任妻子為他帶來的三個繼子。
[2]摘自金魚J整理的哈內克訪談。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