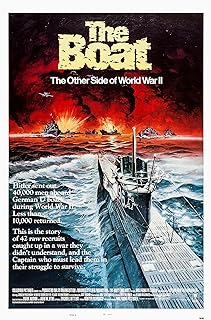電影訊息
從海底出擊--Das Boot
編劇: 沃夫岡彼得森
演員: 約根柏契納 Herbert Gronemeyer Klaus Wennemann Hubertus Bengsch Martin Semmelrogge
![]() 8.4 / 264,214人
149分鐘 | 209分鐘 (director's cut) | Spain:138分鐘 (VHS version) | USA:239分鐘 (special uncut DVD version)
8.4 / 264,214人
149分鐘 | 209分鐘 (director's cut) | Spain:138分鐘 (VHS version) | USA:239分鐘 (special uncut DVD version)
編劇: 沃夫岡彼得森
演員: 約根柏契納 Herbert Gronemeyer Klaus Wennemann Hubertus Bengsch Martin Semmelrogge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3-10-18 18:26:48
經典源於細節——以幾個人物形象為例
本文的配劇照版,請查看http://www.douban.com/note/314030943/,
轉載請註明作者。【以下內容有劇透】
作為一個關注細節的人,我在看Das Boot這部電影第一遍的時候,為整部影片安插的細節之多,感到非常吃驚。這之後我又聽了導演評論音軌,在裡面,導演沃爾夫岡•彼得森強調了這部電影是基於「讓片子裡的每件事物都有意義」的理念製作的,「而不是類似於,『等著看會發生什麼吧』」。聽到這裡,我又重新看了這部片子第二遍,很高興地發現了一批看第一遍時沒能注意到的細節。可是當我看到第三遍、第四遍乃至更多遍的時候,新的細節依然層出不窮,讓我開始理解這部已經有30年歷史的影片,依然歷久彌新的原因。從某種角度說,影片的創作者就像是打造了又一個沉沒於海底也不會被海水碾成碎片的、牢固可靠的U潛艇,種種細節充分展現了其工藝之精美,以及內涵之深遠與豐富。
整部電影非常嫻熟地使用了兩個看似普通,卻異常有效的敘事手法:對比與重複,在五位主要角色中安排了三對比較——艇長與輪機長、大副與二副、沃納少尉與上述四者;通過不同的時間節點上人物的不同行為,刻畫他們的成長與發展;通過重複以往的場景與對話,重申人物不變的主導性格與動機。
如果說性格刻板、生活潔癖的大副與狡黠樂天、不拘小節的二副這對人物的對立是顯然的話,艇長與輪機長表面上不存在任何對比。他們同樣的經驗豐富,又同樣愛艇如家,同樣具備關鍵時刻「扶潛艇於將傾」的能力,也同屬於日漸衰微的「alte Gang(老一群)」,面臨被「嘴上逞英雄」的新一群所取代的悲劇。然而影片的創作者們希望經由本片塑造的,顯然是擁有不同主導個性的兩位不同人物。在兩位主要角色擁有一大批重合的個性背景的情況下,就尤其需要安排細節以區分二者的不同。在這裡只簡略提兩個表面上完全不影響劇情的小枝節。首先是他們軍裝外套下所穿的襯衫具有截然不同的主導色——輪機長為代表熱情的紅,艇長為代表沉靜的藍色。這顯然是服裝部門的特殊用心:當輪機長身穿一件紅藍色格、紅色為主的襯衫的時候,艇長有時穿著一件藍白格襯衫,有時穿著純藍的襯衫,有時穿著一件紅藍色格、藍色為主的襯衫。在輪機長穿著一件血紅色的毛背心的時候,艇長也會把深藍色毛外套穿在裡面。當輪機長捧著泛黃的照片,完全被對妻子的思念、對回家的渴望擊倒時,只有刺眼的血紅色毛背心能從色彩上加重這一強烈的思緒;在潛艇沉於海底,無處不需要維修時,紅藍格襯衫又變成了可以最準確地表達忘我工作與沉著應對在輪機長身上的統一的意象。側面印證紅藍色比喻義的另一個證據是,在艇長唯一一次相對魯莽地在暴風雨中進攻驅逐艦的場景中,他自始至終戴著一條印有明顯紅色花紋的圍巾。這條圍巾此後只出現過一次,就是在艇長因為與其他U潛艇航線重疊而暴怒的時候。所以說,紅色在本片中是代表衝動與激情的視覺語言,使得輪機長之性情與艇長之冷靜得到區分。作為輪機長最真摯的朋友,艇長在接到穿越直布羅陀的自殺式任務後,很快拍出更換輪機長的電報,理由是「Der Leitende ist fertig(輪機長累了)」,所以「Er muss von Bord(他必須上岸)」。隱藏在這些對話背後的事實是,艇長本人是永遠不會將「累」的一面展現於外界,也不需要任何人幫助他「上岸」的。這並不是指他冷漠無情,否則也不會有聽香頌唱盤,或者與無線電員亨瑞希交心的情節。只不過相對於輪機長,艇長無處不在的沉靜與客觀,導致了他遠沒有前者那麼多的維繫於「岸」上的感情羈絆。
第二個可以充分展現輪機長與艇長區別的細節,是二者與沃納少尉在影片一開始時,面對掀翻一桌酒瓶以搏眾人一笑的二副,通過不同的面部表情,所做出的不同反應。沃納少尉的肢體語言摻雜著愉快、興奮與好奇,顯然覺得這位陌生的中尉是個有趣的人。艇長既沒有微笑也沒有皺眉,像是認定了二副的所作所為既不足為惱,也不足為奇。最微妙的是此時掛在輪機長臉上與前二者形成鮮明對比的,因為打電話受阻的焦慮,而顯得有所遷怒的神色。全片中類似這樣的片段,還有輪機長猛然聽見廣播裡播放的軍歌,狂躁地命令 「Abstellen(關上)」;聽到英國皇家空軍空襲科隆的消息,他把咖啡杯重重地撂在了桌子上,心急如焚地徑直走出了軍官艙。在這些場景中,他的本意絕不是怠慢尋歡作樂的二副、無辜的亨瑞希或者坐在一旁的另外四位軍官,而只是本著至性至情、忠於內心感受的主導性格行事的結果。順便一提,上述三個場景中的兩個,他在土黃色軍常服里穿著的,都是那件紅藍相間、紅色為主的格子襯衫。
另外一對已經提及的對比,就是刻板到「可以用後面夾堅果」的大副和想出這句玩笑話的二副。此二人的對立簡直就像水與火:海歸報效祖國的大副身高超過一米九,滿口方言的二副身高不足一米七;大副談及宏偉的志向與高尚的理想時,二副總在一旁瞪大了眼睛吃驚地盯著他看,二副笑鬧耍寶的時候,大副一般也在背後冷冷地旁觀。有一個細節是,二副在酒吧捉弄歌女的同時——據導演評論音軌所述,連飾演歌女的法國女歌手事先都不知道二副打算開的玩笑是如此出格——大副卻在遠景處倚著一扇門的門框,自始至終不帶一絲表情地凝視著眼前的這場喜鬧劇。為了突出這個角色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大副在四個小時的影片裡就很少穿與艇內其他人相同的衣服,罕見的幾次與人衣著相同,卻都是與二副身著相同款式的軍常服,不過二人的天差地別同樣可以體現在領帶的系法、襯衫的整潔與否甚至是徽章的光亮程度上。在二副非常滿足於生活中平庸的樂趣的時候,大副卻幾乎已經不屬於這個俗世了,因為縱觀全片,他幾乎沒有吃飯。誠然,他沒有缺席過一次片中所鋪陳了的正餐,並且總要以誇張的餐桌禮儀震懾住不夠講究的艇長、輪機長、沃納少尉與二副。但是且看他在四次正餐中吃進了什麼——
主餐為羊排的第一餐,大副用刀叉細細地分割成塊,還沒等吃就滿腔熱情地去值第一班觀察哨;
主餐為魚的第二餐,大副用刀叉完美地剔到骨肉分離,還沒等吃就被艇長攆去放英國軍歌;
主餐為豬肉的第三餐,大副用刀叉耐心地把沒長毛的部份挑了出來,還沒等吃就被輪機長騙去找了醫生;
在「維悉號」上的饕餮,鏡頭的右側,大副拘謹地拿著一截類似於瓜條的東西往嘴裡送,鏡頭的左側,二副已經大半隻雞腿下肚。
儘管錯過了所有正餐,大副對另外四人吃布丁、榨檸檬汁、喝咖啡的「小灶」行為依然毫不熱衷,他寧願在一旁向見習軍官烏爾曼口述自己對於軍容軍紀、軍事領導力的思想認識。烏爾曼是一個我還想在後文中加以詳述的角色,但此處代表著艇上唯一一個還能買大副帳的人。但是兩次「小灶」情節過後,本片細節的威力又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前景中,艇長、輪機長、二副與沃納少尉聊著他們的話題,背景中,烏爾曼開始發愣打呵欠,直到被大副催促,才磨磨蹭蹭地拿起筆在本子上謄寫,暗示了這位唯一熱心的聽眾也已經流失。 那麼大副有沒有哪怕一瞬間放下他這種近乎於「存天理,滅人慾」的架子呢?事實上是有的。假如仔細觀察五位軍官在「維悉號」上是如何對待他們手上的香檳,可以發現艇長、輪機長和沃納少尉僅僅抿了一口,大副和二副卻痛快地把一整杯都喝乾,只不過前者是出於總算見到一批熱忱的納粹的「快慰」,後者則是在任何權威面前都能本色不改地行事。
另一個有關大副的極其微妙的細節,是他身為一個本身的存在就能給人帶來不快,總在蔑視他人甚至常常在害人的納粹分子,卻一次不落地參與到了三段和救人有關的情節中。如果目的只是簡單的讓這個「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捲入戰爭醜陋、消耗、完全不光鮮的一面,則只需安排他在一旁驚恐地旁觀便足夠了,沒有必要變成三次不遺餘力地出手相助:首先是派格姆滑落甲板的一次,大副幫助把他抬到控制室的一個平面上,為此濕透了衣服;第二次則是配合兼職醫生的亨瑞希,挽救重傷的領航員Kriechbaum;最後一次是空襲後躲在掩體內,他試著為被彈片擊中的水手長止血,又一批炸彈落下,弄得所有人渾身落灰的時候,他反而是為傷員殿後的那一個。這些都是本片在電影創作空間內的自由發揮,但事實上已經大大地偏離了原著小說作者Buchheim的本意——在原著小說里,Buchheim連最後一個諷刺這一角色的機會都沒有放棄,在重返拉羅謝爾的航程中,還記述了一次此人「足以上軍事法庭」級別的重大失誤,並反覆使用「unfähig(不稱職)」一詞用於貶低。而在電影裡,艇長對大副所下的「判詞」只有「Kinnmuskelspanner, junger Marschierer, weltanschaulich durchgeformt(自以為是的人,年輕的進軍者,世界觀被塑造了)」,有必要注意的是,這些評價沒有一個同艇長抨擊拉羅謝爾酒吧裡的年輕軍官們的用詞重合:「(jetzt kommen) die Quexe, die nassforschen Typen, Maulhelden(盛氣凌人的一群,嘴上逞英雄)」。這就又涉及到一個回答起來或許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容易的問題:片中的大副,到底是不是一位Maulheld?從艇長與大副在第二次用正餐時劍拔弩張的言詞交鋒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艇長在蔑視地說出「Maulhelden, nichts als Maulhelden, allesamt」一句時,「allesamt(所有人都是)」也把大副包括了進去。但是我卻認為,本片中真正按照Maulhelden定義塑造的,只有拉羅謝爾酒吧里喧鬧的軍官,以及「維悉號」上那批跳樑小丑一樣的船員:艇長給予這批人的一律只有冷峻的面部表情加之輕蔑的眼神——在拉羅謝爾酒吧,他評論醉酒的「新英雄」的措辭之嚴厲,與此前先後三次容忍了酒後胡鬧的艇員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維悉號」上,他連禮貌的微笑都不屑施捨給好奇心過剩的艦長。相比而言,艇長在對待大副的態度上,就相對軟化得多。就算只是出於充分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戰鬥集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行事,我也不相信鄙視Maulheld者如他,會在深陷海底時主動坐到一位Maulheld身邊,談論分米波、厘米波或者任何別的問題。再考慮到本段開始時提到的,電影創作者在很多細節中為大副設定的良知尚存的立場,我認為本片對大副的判斷停留在「weltanschaulich durchgeformt(世界觀被塑造了)」的層面,雖說有過度理想化之嫌,但對於一部電影而言,未必不是一個討喜的設計。
更何況,與小說中的大副不同,電影裡的大副在海巡過程中逐漸走上了反思與救贖的道路。在導演評論音軌里,影片播放到「維悉號」上的盛宴,製片人提醒觀眾注意艇上軍官們蒼白的臉色與凌亂的鬍鬚,以及大副是唯一一個還注重儀容儀表的人。導演隨即補充道:「但他也開始瓦解了。」正如這句評論所揭示的,接到穿越直布羅陀的指令的一刻,也標誌著大副這一人物形象的重塑。他停止系領帶,臉上開始有胡茬,長出黑眼圈,最終在險些沉沒海底的一戰中,實現了朝著艇上普通官兵形象的回歸。一個只在未剪版中保留的,大副怔怔地擦著望遠鏡,衣襟上還沾著救助Kriechbaum時落上的鮮血的鏡頭,傳達了很多這位常常被人簡單地歸納為「艇上唯一的納粹」的「扁平人物」的更深層面的資訊。幾個大副如何對待自己胸前掛著的望遠鏡的細節,暗示了這個表面上不近人情、不通常理的人物,在內心裡最為認同的是自身作為「第一觀察員」的職責所在:偷襲護航船得手後,英軍驅逐艦開始追擊潛艇,艇長摘下了胸前的望遠鏡,大副把手向上移了移,揪著帶子,但終究沒有動手摘,一直戴到了沃納少尉已經帶著赴死的心理準備,在大副的舖位上昏沉睡去(個人認為,這實在略帶諷刺——躺在「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的舖位,而這位「領導人」本人,倒可以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艇長在維哥港口尋覓「維悉號」所蹤,在指揮室和其他人一起等候的大副,赫然換上了最正式的那套軍禮服,但胸前的望遠鏡,只是在兩個引擎全部關閉時才離身;第三次便是在積水的困境中,下意識地一次又一次擦拭這件在深海中已經淪為裝飾的工具。如果說大副還有什麼過於常人的優點,我認為只可能是畫海圖——潛艇出航一段時間,卻屢屢接不到任務的時候,艇長在航海圖上用圓規畫了八九段等距線之後,宣佈「路程太遠,趕不到(支援馬坦的潛艇)」,輪機長沮喪得用帽子拍擊大腿,大副卻面有疑慮地走到海圖邊,想必是拿起圓規重新畫了一遍;此外則是未剪版中輪機長做出「考慮到燃料問題,我們甚至開不到拉羅謝爾」的表述之後,大副在控制室裡心無旁騖地畫著海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測算憑藉現有燃料順利開回拉羅謝爾的可能性。但是在深海沉船的前提下,假如有比望遠鏡更無助的工具,恐怕就是圓規了。鑒於上述兩點,我感覺大副對潛艇命運的缺乏信心,與其說是出於泛泛意義上的英雄主義幻想的破裂,不如說是出於他所具備的本領的無事於補。不僅如此,我認為大副的英雄主義理想非但談不上破裂,他甚至有幸目睹了自己曾經親口提到的一種理想境界變成了現實。在烏爾曼還樂於奮筆疾書地記錄的一段心得體會中,大副曾說:「在投向指揮官的凝視中,只剩下一個古老的、彰顯著終極的信賴的問題:『長官,你要求我們在哪裡去死?』……」而這恰好是「浪子回頭」、「戴罪立功」的約翰在完成了他的救贖後,投向曾經慷慨地寬恕他的艇長的眼神。站在艇長背後的大副看到了,所以他感慨地微笑了,唯一一次既不帶有驕傲也不帶有譏諷地微笑了。這之後,他也通過監控受損情況,以及堅守值班崗位的方式,完成了屬於自己的救贖。就如同他出現於穿越直布羅陀之後的每一個鏡頭中都不是偶然一樣,他的形象定格於艇長迎著翻滾的浪潮,暢快地大喊「Not yet, Kameraden! NOT YET!」這最著名一幕的背景中,也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一種脫胎換骨和蓋棺論定。大副確實洗心革面了——還是在字面意義上的,因為在逃離直布羅陀「漏斗」之後,他真的徹底不再刮鬍鬚了。
另一位與艇上所有軍官形成對比的人物,是隨軍記者沃納少尉。本片的創作者曾經在是否使用第一人稱敘述的問題上舉棋不定,最終只有未剪版沿用了這一構思。但很顯然,即便在放棄了第一人稱敘述的導演剪輯版和影院版中,沃納也相當於觀眾的眼睛。當沃納的雙眼兩次出於絕望而閉上的時候,艇上絕望的尖叫與無助的哭喊也戛然而止,留待沃納再次醒來時,重塑恍然如夢的劫後餘生場景。作為全片中戲份第二多的人,這位隨軍記者卻不具備哪怕一個主導的性格特徵:他既不果決,也不勇敢,沒有過人的才智,也不幽默樂天;他沒有描述過入伍前的經歷,沒有鋪陳對戰爭的認識,沒有解釋對另外三位「准反法西斯分子」的容忍是怎麼同他的宣傳機器的身份取得的一致;前一分鐘還在饒有興緻地期待二副開更多的玩笑,後一分鐘就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輪機長的疲憊的心緒。如果這個人物還受哪個動機引導的話,那一定是「不要錯過眼前的所有一切」,他在體驗的層面,做的比反思更好。由此,我認為沃納就是大螢幕前的每一位觀眾在本片中的投射。假如非要指出沃納有別於其他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有一顆容易同情別人的心,而這恰好也是電影觀眾作為一個整體普遍具備的唯一特點。沃納可以輕易被帶入別入營造的氣氛,就像在Probealarm(測試警報)時,他緊張得不能自己,反應比影片末尾潛艇沉入深海還要強烈;聽到見習軍官烏爾曼所講述的未婚妻的身世命運,沃納給予了很多同情,並且主動提出在上岸後替烏爾曼寄出那一大沓信——就像一個一般觀眾會去想、去做的那樣,但付諸影評人筆端,這段劇情就被不留情面地詬病為全片唯一的cliché。
沃納以隨軍記者的身份,滿懷好奇心地隨這艘潛艇一起遠航,但他畢竟是個外來者。明里,他被稱之為客,享受到很多別人無法獲得的照顧;暗裡,也偶爾遭到老兵欺負。在指令室的艙口,他的每次請示「Mann auf Brücke?(請求上艦橋?)」,如同請求一扇緊閉的門背後的對方允許,以便一睹掩蓋於其後的所有神秘。隨著航程越來越遠,沃納,或者說他所代表的觀眾,與潛艇的其他官兵遭受的磨鍊也越來越多。飽經了風霜洗禮,他們盼望自己能在求生的鬥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影片給了他們機會——在最後一次也是最重大的事故發生後,沃納舉著照明燈與約翰反覆鑽入冷水,彌補了艇身的所有漏洞。當約翰向艇長報告,所有進水處封堵完畢後,艇長的聲音哽咽、眼圈濕潤了。「Gut, Johann.(好啊,約翰。)」他停頓了一下,「Sehr gut.(太好了。)」這裡,一個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sehr」,卻遠不是隨隨便便插進文本中的。初看時,我理解它是說給絕望中的轉機,也是說給「浪子回頭」的約翰聽的。但比對十幾個小時的搶修全部完成後,同樣是艇長說給絕望中的轉機,說給幾近勞心至死的輪機長的「Gut, ... Gut.」我意識到,這個意義深遠的「sehr」,一定也是說給站在約翰背後,在寒冷中顫顫發抖的沃納,以及移情於其中的每位觀眾聽的。這也是屬於他們的勝利。
在艇上的士官人物群像里,輪機室裡的「Gespenst(鬼魂)」約翰,有著謎一般的、充滿了矛盾的人物形象。往簡單的方向理解,約翰對潛艇的柴油發動機有著「准戀物癖」一般的依戀。導演剪輯版和未剪版中的一幕顯示,這位主機械師連睡也睡在嘈雜的引擎邊。未剪版還保留了一段大副準備去輪機室找艇長匯報事項的情節,他花了很大氣力才擰開通往輪機室的艙門,暗示了外表的體面與光鮮在輪機室的一錢不值。能駕馭這方狂暴的天地,並且深得其中樂趣的,只有約翰。但就是這樣一個與人溝通有礙,與鋼筋鐵臂交流卻無妨的人物,卻難敵自己內心的恐懼,穿著逃生用的充氣背心,直奔指令室的艙口,險些爬上梯子,打開艙門,讓全艇人死個乾脆。目睹這一事件的艇長,只能用頹然無助的語氣喟嘆:「Ausgerechnet Johann.(在所有人裡,(怎麼會)是約翰。)」此後,艇長在另一情節中更是重複了上述感慨。從常理角度,一個把輪機室視作家的人,無論如何不會選擇在死亡降臨之前,離開自己的「戀物」對象和「舒適區」,反而求諸危險的真正所在——艦橋艙口。對此,我只能理解為導演故意選擇背離人物性格特徵的行為,反映死亡的恐懼是多麼輕易地把人壓垮,在一次次的聲吶探測與深水炸彈襲擊中,將理智與情感全部交還給求生的本能。
約翰之所以得名「鬼魂」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三個。首先是上文已經提到的,他跟引擎的交流比跟人的交流更融洽,這點決定了外界對他的「非人化」已經無可避免。其次是在夜幕降臨之時,他確實總會變得異乎尋常地興奮,兩次夜間進食就是很好的例證(其中一次只收錄於未剪版)。第三點也是很細節的一點,就是約翰行走坐立事實上都和軍人作風相差太遠。單說約翰的「站」,那絕對是典型的「站無三分直」,在出海的一場戲中,不妨仔細看看是誰頻頻摘下帽子,朝岸邊的送行人揮舞,是誰誇張地爬到艦橋的護欄上,和湯普森艦長揮手道別。對準約翰的鏡頭往往是特寫加仰拍,有意渲染一種不穩定感。飾演約翰的演員那種神經質般的枯瘦,也讓他的筋骨看起來就像是老樹上的結節。種種這些都在暗示觀眾,眼前的這個人好像確實來自另外一個世界。
有趣的是,作為「人」的約翰卻與作為「鬼」的約翰又有著天壤之別。一種在全艇其他成員身上都無法找到的氣質,深藏在約翰習慣性的眼瞼低垂後面。在約翰首次和全體官兵一起登場,艇長介紹沃納少尉的情節中,艇長談及:
「Wir haben einen Gast an Bord. Leutnant Werner, Marinekriegsberichter. Will sich bei uns ein bisschen umsehen.(我們艇上有一位客人。沃納少尉,海軍隨軍記者。他想觀察一下我們。)」
士官們紛紛扭頭打量沃納,二副朝沃納咧嘴一笑。反觀約翰,雖然臉上也帶著笑容,但同時也把視線深深地垂了下去,與眾人形成極大的反差。
第二次則是聽到艇長哽嚥著聲音,給予他「sehr gut」的讚揚,在隨後的特寫鏡頭裡,約翰的視線反倒先是望著地板,然後揚起看了看艇長,眼珠轉動了幾下,像是欲言又止,很快又把視線轉向了下邊。未剪版本中,艇長找約翰討論柴油機油耗的一段,更是上述場景的翻版,整整兩分鐘的時間裡,約翰就很少把頭仰起來。
飾演約翰的演員很會通過眼睛演戲。而他眼中天生帶著的驚恐,更是為角色的塑造加分不少。即使是沒有台詞的時候,他也能通過雙眼表達出細微的感情。比如這一人物第一次經水手長介紹給沃納,也相當於介紹給螢幕前的觀眾的時候,水手長半打趣地打招呼,「Na Johann, alles schön geschmiert?(機器都潤滑了吧?)」約翰伴隨著輪機室的巨大噪音轉身微笑,緩慢地眨了眨眼,以表肯定。在向艇長致歉的情節中,約翰眼神中的惶恐與羞赧,為他言不成句的申辯做了餘下的發言。或許艇上為數不少的官兵都能被稱為心地誠懇,有同情心,嚮往和平,富有良知,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以「迎戰」的硬漢心態面對生活、面對命運和所有一切。假如必需要找出一個羞怯與內斂個性的代言人的話,只能是輪機室的鬼魂——約翰。
最後我想說說讓我感到不滿意的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扁平人物,烏爾曼。讓我們來看看烏爾曼在整個出海過程中都做了什麼:偶爾在值觀察哨,常常在寫信;身為見習軍官,卻只有大副向他灌輸一些過於理想化的價值觀,其他三位軍官,尤其是艇長,不僅不曾對他加以任何指導,甚至都沒有過直接交流;在油輪沉沒,船員紛紛落水,面臨溺亡的命運時,他在艦橋上啜泣(我又覺得此情此景有點諷刺——電影中著力塑造的角色,對戰事的變化沒起什麼關鍵作用,哭泣時反倒不落入後);在潛艇深陷直布羅陀海底的時候,這位見習軍官躺在舖位上茫然無措,在艇長下令把水引到控制室後,才加入了拎水桶的隊伍;最後他死了。如果這還不算缺乏性格的話,我不知道要怎麼樣才算。尚且不提在直布羅陀海底的束手無策,是一個給人物加負面分的劇情,因為無所事事在彼情彼景中,已經是僅次於「講福音」的、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
在導演評論音軌的最後,沃爾夫岡•彼得森介紹說,U-96潛艇官兵的最終生死存亡,是由他的妻子Maria一手敲定的。一開始的時候,我意識到這種命運安排不是出於抽籤式的偶然,卻難以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所在。直到後來不知道看到第幾遍的時候,這個問題忽然迎刃而解。這場歷史中並不存在的空襲,存在於本片的意義是為了突出戰爭的無情與荒謬。為此,導演犧牲了所有主觀上並不具備強烈的反抗精神,而更像是完全被動地絞入這場戰爭的人,在故事裡,是性格最為平和的約翰、烏爾曼和「講福音的朋友」,在和平年代,可能就是螢幕之外欣賞這部電影的你我他。至於為什麼遊戲人生的二副也要承擔這一命運?查詢一下1941年冬季第三帝國的U潛艇海巡記錄就會知道了:全艇的軍官中只有當時的二副生卒年月不明,其他成員如戰後改任商船船長的艇長,以及回到墨西哥城的大副,甚至見證了本片1981年的拍就與上映——這種登峰造極的對細節的尊重,只能用嘆為觀止來形容。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