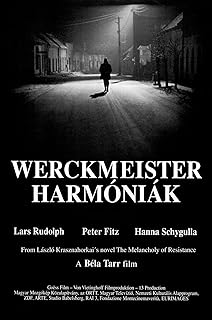電影訊息
鯨魚馬戲團--Werckmeister harmoniak
編劇: Laszlo Krasznahorkai
演員: Lars Rudolph Peter Fitzpatrick 漢娜席古拉 Janos Derzsi
鲸鱼马戏团/残缺的和声/和睦相处
導演: 貝拉塔爾 Agnes Hranitzky編劇: Laszlo Krasznahorkai
演員: Lars Rudolph Peter Fitzpatrick 漢娜席古拉 Janos Derzsi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3-03-21 06:04:12
聚焦人民的鏡頭
貝拉•塔爾一生都在努力將他的鏡頭對準人民,和塔可夫斯基一樣,他在對待藝術上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他年輕時也曾和當局針鋒相對,甚至因此入獄。塔爾不懈地用他那充滿藝術魅力的黑白影像和幾乎完美的長鏡頭讓全世界關注的目光集中在被邊緣化的東歐國家,他的影片是東歐人民真實生活的寫照,展現了嚴酷的現實和人們苦難的命運,探討著國家、社會和人性之間的聯繫和衝突,飽含著對歷史的反思和對制度的批判,喚起人民對自我乃至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充滿著寫實主義色彩和強烈的人文關懷。《鯨魚馬戲團》是塔爾繼其巔峰之作《撒旦探戈》後又一部力作,影片耗時四年,先後與7位攝影師合作。在這部電影中,用光、佈景、場面調度和攝影處處透露了塔爾大師級的處理手法,加之對充滿質感的黑白影像的純熟運用,使得整部電影富有極其深刻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
開篇第個一鏡頭是整個影片的引子,Janos指導幾個醉漢模擬天體運轉,用詩一般的語句描繪著宇宙永恆的和諧。日蝕突然出現,在那一瞬間,地球上的生命陷入恐懼;隨即月亮移開,黑暗消散,萬物被拯救般地重獲呼吸。Janos的發音和手勢散發著令人著迷的魔力,貝拉•塔爾的御用配樂師Mihaly Vig的配樂每個音符都觸碰著心靈,那簡單、純淨、不斷循環的節奏把觀影者帶入一種冥想的狀態,彷彿置身於闃靜的宇宙之中。接著,Janos合著音樂的旋律哼鳴,為這個緩慢運動的體系所陶醉,燈光和鏡頭的旋轉營造了靜謐和渺遠的氛圍,流露著對創世的敬畏以及對浩瀚星系中渺小生命的靜默。在這個奇異又迷人的畫面里,用鏡子乎達到了完美:日蝕出現,太陽的光輝消失之時,鏡頭在拉遠的同時緩慢上移,這樣一來,影片的視角從主角所引領的作為觀者的我們的眼中移至一個更高的俯瞰式的位置,猶如上帝的眼睛在注視著發生的一切。美妙的是,這一意境的過渡只不過是一個長鏡頭連續拍攝過程中機位上移了一點點而已。這時,酒館老闆突然打斷演出,趕走Janos,把角色和觀眾一併帶到現實中。Janos說:「一切都還沒有結束。」這句話啟示了之後發生的故事。
Janos是一個卑微的小人物,他安份守己地生活,夜裡做分發報紙的工作,並盡職地照顧德高望重的隱居音樂家Eszter,他生活拮據,但卻毫不猶豫地花錢觀看鯨魚,說明他懷有希望和信仰。Janos遁入黑夜的鏡頭展現的是他的悲憫、虔敬和充滿希冀。他卑微的身影緩緩渡過黑暗,彷彿踏過幽謐的歷史的河流。影像表現出極度的孤獨,透露著悲涼的歷史感和命運的沉重感。這裡再次顯示出導演在光線運用和鏡頭調度上的功力,鏡頭一再拉遠直至人物晃動的身影成為黑夜中的一個點,似乎昭示著微弱的信仰之光最終將湮滅在歷史深邃的黑洞之中。鏡頭向後推移過程中緩慢壓低,致使大面積的黑暗包圍行走中的Janos身邊的一小塊兒高光區。這一場景的寓意十分豐富,每一個人類的個體都是歷史寒夜中的淒淒光點、但光亮再弱,黑暗卻也無法將其全部吞噬(下一個場景緊接著轉換至次日Janos面向朝陽行走,再次顯著地暗示了希望的延續)。在整個長鏡頭的時長里,黑白影像和主題音樂再現使得電影語言直入骨髓。
第二天,Eszter在麥克風前錄下自己的獨白,有著啟示錄的意味。實際上,Werckmeister的音律學說並不是打破了所謂的「純律」的和諧,相反,正是為了修正「純律」和弦中的不和諧音素進而創造了更加旋律化的音程。這樣看來,筆者更傾向將電影題目Werckmeiste Harmonies理解為人們在變革中尋求秩序與和諧的所為。Eszter認為,應回到畢達哥拉斯的時代,但這個理想與群體、種族、社會之間存在必然的矛盾。畢氏重視人的價值,鼓勵積極的人生態度,崇尚在家庭、團體、組織、國家、乃至國際聯盟的種種制度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諧發展。事實上,在制度之下,人作為一個個體和人所組成的群體這二者該如何去從,這個題目已隨著故事的推進自然地融入到了情節的發展之中。探尋個體、群體和體制三者間關係以及這三者在歷史進程中乃至未來社會發展中各自的定位是這部電影的主旨。
Janos和Eszter,一個青年,一個長者,他們好似游離於階級之外的弱勢個體。但其實兩人之間卻有不同:Eszter看清了一切問題的本質,並揭示出了真相,但他已別無他念,只渴望歸隱音樂,不被打擾地潛心研究和創作。而Janos尚有信念,他的內心純淨質樸,懷著單純和幼稚的願望。影片中段,兩人完成Eszter前妻以要挾破壞其生活為條件交予的任務後分頭離開,鏡頭從平行位置逐漸拉升,注視著他倆各自踏上分岔路。鏡頭是遠景,但卻反而增強了畫面的飽滿度和表現力。處於無奈而妥協的Eszter無心傾聽村民的訴苦和抱怨,他已身心疲憊,只渴望回到自己與世隔絕的住所;前去交差的Janos也舒了一口氣,自己的生活終可以恢復往日的平靜,雖然乏味卻安穩。然而,在兩條路的盡頭只有宿命的悲劇在等待著他們——Janos受到打擊後成為精神病患者,Eszter的家被前妻和警察局長霸佔。
兩個孩子發瘋的橋段暗示暴亂前的動盪不安,警察局長酒後抽風的情節則刻畫了另兩類群體,即體制內的麻木者(警察局長)和追求利益的局外人(Eszter前妻)。
前後兩段廣場戲展現的是人們的不知所措。沒有方嚮導致盲目的行動,無知帶來的是無辜的犧牲。洗劫醫院前,導演用一個很長的鏡頭刻畫滿懷忿恨的群眾的群像,鏡頭前後推拉、上下移動。人們的呼吸急促,步伐堅定,凸顯出人作為個體的強大。這裡,再次點出了導演所關注的核心:無疑,人類是宇宙中最具生命力、且唯一真正擁有並懂得如何運用力量的生物,但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的力量究竟該如何運用?運用到何處?怎樣用這力量去捍衛自我、去鬥爭、去革命?進而去改變和創造而不是去顛覆和毀滅。很顯然,在各種體制和制度之下,蠻力的盲目爆發導致人民自身白白地成為可憐的歷史犧牲品。這一悲劇性在暴亂者目睹浴缸中嶙峋老人的一幕達到頂點,導演布設耀眼的白熾光打亮老人所在的一整塊空間,和黑色的前景形成強烈的反差。經受了時代的鞭笞和命運枷鎖的束縛與折磨,奄奄一息的老人虛弱的身軀赤裸地呈現在同樣正在經受著上述遭遇的無辜的施暴者眼前,我相信,這裡並不是無情的批判,而是炙熱的關切。動亂結束後,攝相機記錄了暴動者拖著身子依次通過迴廊,高反差的黑白影像使人物形成剪影效果,生動地體現了他們同為受害者的形象。隨後,鏡頭下移並俯拍一個個垂喪頹敗的身軀和緩緩移動的沉重的步伐,再次勾勒出由「暴徒」變為最終的犧牲品的群像。
回眸歷史,從「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十月運動」、「波茲南事件」到「東歐劇變」,一次次革命的爆發和政治格局的演變是否是歷史的進步?一再以武力方式終結現有制度或秩序難道就是所謂歷史的必然性?既然無法確定新制度的正確性,革命也就全無意義,亦可謂是失敗的,然而,這種失敗究竟是源于思想體系的錯誤還是階級的侷限性?
當個體會聚為群體,人們升級為人民,他們卻不知該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去主宰自己的命運。印刷廠的女工對即將發生的革命的不安和恐懼;Janos房東的老婆對丈夫的行為表示不解和擔憂;餐廳肥胖男子一邊進食一邊與女人親熱展現的是受慾望支配的木偶般的軀殼;馬戲團老闆因害怕出亂子而拒絕演出;他的助手為牟取經濟利益想要和王子單幹;似乎高貴的王子也不過是一個被操縱和利用的乾癟的皮囊。正如影片中所述:「一切都是幻覺,一切都是虛無,一切都沒有意義。」
充當佈道家的王子無法充當指引人們的現實領袖,剩下鯨魚淪為信仰被扼殺後的殉道者。影片的結尾,卡車車廂綻開在滿目瘡痍的廣場中央,鯨魚裸露著的衰敗的身軀癱軟成一副泥像。神秘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鯨魚的眼淚——上帝為人類而流的淚,亦是導演理性關注的眼淚。Eszter作為見證了悲慘歷史的老人,再一次見證了悲慘的現實。他在離去中回望鯨魚,畫面停滯。至此,這個以犧牲為代價卻仍未能找到出路的短暫的插曲必將再一次成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開篇第個一鏡頭是整個影片的引子,Janos指導幾個醉漢模擬天體運轉,用詩一般的語句描繪著宇宙永恆的和諧。日蝕突然出現,在那一瞬間,地球上的生命陷入恐懼;隨即月亮移開,黑暗消散,萬物被拯救般地重獲呼吸。Janos的發音和手勢散發著令人著迷的魔力,貝拉•塔爾的御用配樂師Mihaly Vig的配樂每個音符都觸碰著心靈,那簡單、純淨、不斷循環的節奏把觀影者帶入一種冥想的狀態,彷彿置身於闃靜的宇宙之中。接著,Janos合著音樂的旋律哼鳴,為這個緩慢運動的體系所陶醉,燈光和鏡頭的旋轉營造了靜謐和渺遠的氛圍,流露著對創世的敬畏以及對浩瀚星系中渺小生命的靜默。在這個奇異又迷人的畫面里,用鏡子乎達到了完美:日蝕出現,太陽的光輝消失之時,鏡頭在拉遠的同時緩慢上移,這樣一來,影片的視角從主角所引領的作為觀者的我們的眼中移至一個更高的俯瞰式的位置,猶如上帝的眼睛在注視著發生的一切。美妙的是,這一意境的過渡只不過是一個長鏡頭連續拍攝過程中機位上移了一點點而已。這時,酒館老闆突然打斷演出,趕走Janos,把角色和觀眾一併帶到現實中。Janos說:「一切都還沒有結束。」這句話啟示了之後發生的故事。
Janos是一個卑微的小人物,他安份守己地生活,夜裡做分發報紙的工作,並盡職地照顧德高望重的隱居音樂家Eszter,他生活拮據,但卻毫不猶豫地花錢觀看鯨魚,說明他懷有希望和信仰。Janos遁入黑夜的鏡頭展現的是他的悲憫、虔敬和充滿希冀。他卑微的身影緩緩渡過黑暗,彷彿踏過幽謐的歷史的河流。影像表現出極度的孤獨,透露著悲涼的歷史感和命運的沉重感。這裡再次顯示出導演在光線運用和鏡頭調度上的功力,鏡頭一再拉遠直至人物晃動的身影成為黑夜中的一個點,似乎昭示著微弱的信仰之光最終將湮滅在歷史深邃的黑洞之中。鏡頭向後推移過程中緩慢壓低,致使大面積的黑暗包圍行走中的Janos身邊的一小塊兒高光區。這一場景的寓意十分豐富,每一個人類的個體都是歷史寒夜中的淒淒光點、但光亮再弱,黑暗卻也無法將其全部吞噬(下一個場景緊接著轉換至次日Janos面向朝陽行走,再次顯著地暗示了希望的延續)。在整個長鏡頭的時長里,黑白影像和主題音樂再現使得電影語言直入骨髓。
第二天,Eszter在麥克風前錄下自己的獨白,有著啟示錄的意味。實際上,Werckmeister的音律學說並不是打破了所謂的「純律」的和諧,相反,正是為了修正「純律」和弦中的不和諧音素進而創造了更加旋律化的音程。這樣看來,筆者更傾向將電影題目Werckmeiste Harmonies理解為人們在變革中尋求秩序與和諧的所為。Eszter認為,應回到畢達哥拉斯的時代,但這個理想與群體、種族、社會之間存在必然的矛盾。畢氏重視人的價值,鼓勵積極的人生態度,崇尚在家庭、團體、組織、國家、乃至國際聯盟的種種制度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諧發展。事實上,在制度之下,人作為一個個體和人所組成的群體這二者該如何去從,這個題目已隨著故事的推進自然地融入到了情節的發展之中。探尋個體、群體和體制三者間關係以及這三者在歷史進程中乃至未來社會發展中各自的定位是這部電影的主旨。
Janos和Eszter,一個青年,一個長者,他們好似游離於階級之外的弱勢個體。但其實兩人之間卻有不同:Eszter看清了一切問題的本質,並揭示出了真相,但他已別無他念,只渴望歸隱音樂,不被打擾地潛心研究和創作。而Janos尚有信念,他的內心純淨質樸,懷著單純和幼稚的願望。影片中段,兩人完成Eszter前妻以要挾破壞其生活為條件交予的任務後分頭離開,鏡頭從平行位置逐漸拉升,注視著他倆各自踏上分岔路。鏡頭是遠景,但卻反而增強了畫面的飽滿度和表現力。處於無奈而妥協的Eszter無心傾聽村民的訴苦和抱怨,他已身心疲憊,只渴望回到自己與世隔絕的住所;前去交差的Janos也舒了一口氣,自己的生活終可以恢復往日的平靜,雖然乏味卻安穩。然而,在兩條路的盡頭只有宿命的悲劇在等待著他們——Janos受到打擊後成為精神病患者,Eszter的家被前妻和警察局長霸佔。
兩個孩子發瘋的橋段暗示暴亂前的動盪不安,警察局長酒後抽風的情節則刻畫了另兩類群體,即體制內的麻木者(警察局長)和追求利益的局外人(Eszter前妻)。
前後兩段廣場戲展現的是人們的不知所措。沒有方嚮導致盲目的行動,無知帶來的是無辜的犧牲。洗劫醫院前,導演用一個很長的鏡頭刻畫滿懷忿恨的群眾的群像,鏡頭前後推拉、上下移動。人們的呼吸急促,步伐堅定,凸顯出人作為個體的強大。這裡,再次點出了導演所關注的核心:無疑,人類是宇宙中最具生命力、且唯一真正擁有並懂得如何運用力量的生物,但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的力量究竟該如何運用?運用到何處?怎樣用這力量去捍衛自我、去鬥爭、去革命?進而去改變和創造而不是去顛覆和毀滅。很顯然,在各種體制和制度之下,蠻力的盲目爆發導致人民自身白白地成為可憐的歷史犧牲品。這一悲劇性在暴亂者目睹浴缸中嶙峋老人的一幕達到頂點,導演布設耀眼的白熾光打亮老人所在的一整塊空間,和黑色的前景形成強烈的反差。經受了時代的鞭笞和命運枷鎖的束縛與折磨,奄奄一息的老人虛弱的身軀赤裸地呈現在同樣正在經受著上述遭遇的無辜的施暴者眼前,我相信,這裡並不是無情的批判,而是炙熱的關切。動亂結束後,攝相機記錄了暴動者拖著身子依次通過迴廊,高反差的黑白影像使人物形成剪影效果,生動地體現了他們同為受害者的形象。隨後,鏡頭下移並俯拍一個個垂喪頹敗的身軀和緩緩移動的沉重的步伐,再次勾勒出由「暴徒」變為最終的犧牲品的群像。
回眸歷史,從「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十月運動」、「波茲南事件」到「東歐劇變」,一次次革命的爆發和政治格局的演變是否是歷史的進步?一再以武力方式終結現有制度或秩序難道就是所謂歷史的必然性?既然無法確定新制度的正確性,革命也就全無意義,亦可謂是失敗的,然而,這種失敗究竟是源于思想體系的錯誤還是階級的侷限性?
當個體會聚為群體,人們升級為人民,他們卻不知該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去主宰自己的命運。印刷廠的女工對即將發生的革命的不安和恐懼;Janos房東的老婆對丈夫的行為表示不解和擔憂;餐廳肥胖男子一邊進食一邊與女人親熱展現的是受慾望支配的木偶般的軀殼;馬戲團老闆因害怕出亂子而拒絕演出;他的助手為牟取經濟利益想要和王子單幹;似乎高貴的王子也不過是一個被操縱和利用的乾癟的皮囊。正如影片中所述:「一切都是幻覺,一切都是虛無,一切都沒有意義。」
充當佈道家的王子無法充當指引人們的現實領袖,剩下鯨魚淪為信仰被扼殺後的殉道者。影片的結尾,卡車車廂綻開在滿目瘡痍的廣場中央,鯨魚裸露著的衰敗的身軀癱軟成一副泥像。神秘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鯨魚的眼淚——上帝為人類而流的淚,亦是導演理性關注的眼淚。Eszter作為見證了悲慘歷史的老人,再一次見證了悲慘的現實。他在離去中回望鯨魚,畫面停滯。至此,這個以犧牲為代價卻仍未能找到出路的短暫的插曲必將再一次成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