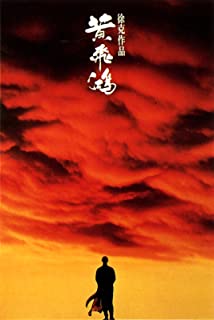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2-12-14 06:28:39
民族認同話語的形成、淡化與重構——淺析功夫電影中民族主義敘事的時代演進
[這是《認同與國際關係》的課程論文,鑒於老師是武術愛好者,我也是,加上功夫電影的民族性,本文的主題應運而生。鑒於本文著意提倡的是徐大導演《黃飛鴻》中的民族主義敘事方式(反思的,多面向的),因此放在《黃飛鴻》的影評下。]
摘 要:功夫電影作為華語電影的一個重要的類型片,從其誕生早期就開始從20世紀初「體育強國」思想中汲取養料,將以「東亞病夫」為代表的民族認同話語內含的衝突結構作為電影表達的慣用主題。但隨著華人文化圈政治氛圍的轉變和經濟的發展,這種民族認同話語逐漸被淡化。到了21世紀,更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異質話語的雙重挑戰,面臨被重構的可能性。
關鍵詞:功夫電影 東亞病夫 自我東方化 民族主義表達
古老的中國功夫之所以致今能有廣泛的影響力,同它與現代電影藝術的結合是分不開的。功夫電影是華語影壇最具國際影響的類型片。而在眾多功夫電影中,那些以近代中國為背景的「國恨家仇」故事,也成為最常用主題之一。而且,功夫電影作為承載近現代中國民族認同話語的一個重要文本,不僅顯示出中國民族主義是近代殖民危機產物的歷史語境,還忠實記錄了不同時代背景下華人對民族主義態度的變化。
通過查閱文獻和檢索据,筆者發現,對功夫片和民族主義相關主題的研究主要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對近代中國人將體育競技與民族主義情緒表達聯繫在一起的現象(「東亞病夫」心結)的分析,主要有兩條路徑:國內過去的研究大多將原因歸結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和壓迫,代表性的著作有高翠編著的《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但近年來一些台灣學者開始嘗試從「身體史」研究的角度和重讀文本的方法,重新回顧這種與身體相關的民族主義認同的發展脈絡,比較系統的研究有台灣政治大學副教授楊瑞松先生探源「東亞病夫」概念的相關論文與專著,以及東海大學黃金麟教授對「身體史」的一些研究著作。第二類是對眾多功夫電影劇情架構、文化內涵以及市場反應的評論。這類文獻多見於不同時期國內各種期刊雜誌,觀點也或褒或貶,不一而足,但在研究功夫電影的社會影響方面,可以算作是第一手資料。第三類是將功夫電影與民族主義敘事聯繫起來的學術性研究。國內在這個主題上的系統性研究相對還比較缺乏,較豐富的是對一部或同一系列電影中民族主義的表達方式的研究,這一主題也散見於一些功夫電影發展史的專著中,如賈磊磊《中國武俠電影史》等都有涉獵,相關譯著也有一些,例如英國學者里昂•漢特的《功夫偶像》。
綜上所述,雖然關於功夫片和電影中民族主義敘事的研究國內已經有比較豐富的資料來源和基礎研究,但將這兩者聯繫起來,旨在釐清20世紀華語功夫電影中民族主義敘事的發展脈絡、探究背後變化動因的研究還是相對薄弱的。本文旨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一些嘗試性的探索。
一、危言:「東亞病夫」、「體育救國」與中國民族主義
功夫片最重要的表現手段——傳統中國功夫,之所以能夠從平凡的民間技藝躍升為「國術」甚至是整個民族精神的寄託,與20世紀初興起的「體育救國」思想是分不開的,而「東亞病夫」這個概念則在這個過程中被反覆言說並成為後來功夫片敘事中的一個重要民族認同話語。
「東亞病夫」一詞現在常被視作列強對中國人身體普遍孱弱的侮辱。西方稱中國為「病夫」據信在國內最早見於1896年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所轉載的政論,但在這篇政論中 「病夫」(Sick Man)僅僅是對甲午戰敗的清王朝積弊叢生、欲振乏力現象的一種客觀描述。事實上中國人用「病夫」一詞甚至更早:嚴復在1895年3月發表的《原強》中就用「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來比喻變法的迫切性和從根本入手的必要性。因此「病夫」最初並非源於西方列強的侮辱,而是在民族存亡之秋一種忠言逆耳的大聲疾呼。
但隨著維新變法運動的失敗,一些知識分子感到要救亡不僅要變法,還要開啟民智民力;同時由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播,剪除國民「劣根性」、與白人爭奪種族優勢的呼聲也逐漸高漲。而「病夫」作為一種所指範疇不明確的日常語言,易作擴大解釋。由是,「東亞病夫」的意涵在20世紀初逐漸發生了改變。1903年,流亡日本的梁啓超發表《尚武論》一文,開始從衛生習慣、傳統道德等方面反思,發出「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的悲嘆。 到了陳天華的《警世鐘》里,開始出現「外洋人不罵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這種將「東亞病夫」界定為外人恥笑辱罵中國人的用語的描述,配合上前述把「病夫」比喻轉化為針對中國人體質羸弱的形容用法的流行,使中國人逐漸將「東亞病夫」理解成西方人對中國人「掛在嘴邊的嘲諷之語」。
為了改變受辱的「東亞病夫」狀態,不少人開始倣傚日本維新中鼓勵尚武精神的做法,將體育作為救國的重要方策之一。梁啓超在1904年出版的《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就明確表達了學習日本尚武強國的觀點。 於是,中國開始出現一些旨在強種救國的的武術團體,其中民間比較重要團體的有1910年創立的「精武體操會」,官方的武術團體則有1928年建立的「中央國術館。然而,民間武術團體的資金和影響力有限,官方的團體不僅困於內部門派紛爭,還缺乏足夠的政治支持,因而在中國「體育救國」的思想最後僅流於空談。
但是,「東亞病夫」概念的變化並導致「體育救國」思想的產生的過程完整地體現了一個國家「自我東方化」的過程,是中國民族主義在外來侵略壓力下產生的一個側面。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通過對原始文本碎片有意無意的擴大解釋和剪切組合,臆想了與國家同樣受辱的、孱弱的中國人群像,然後意圖用相應的恥辱感激勵全民族奮發的精神,實現對西方世界的反抗。雖然「體育救國」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失敗了,但這種要在身體上戰勝東西方列強的思維方式卻遺留在中國的各種小說、傳奇等社會記憶之中,這也成為後來功夫電影中民族主義表達的源頭。
二、形成:李小龍電影中復仇式的民族主義敘事
1930年國民黨當局以有傷風化為由禁拍武俠片後,上海一部份電影製作者開始向香港轉移。1937年抗戰爆發、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和1949年共和國成立,分別造成了三波大陸電影製作人才、資金向香港的遷移。內戰結束後,大陸和台灣都有較嚴格的電影製作和審查制度,相較而言港英當局的審查要寬鬆得多。加上廣東本來就是武術之鄉,各類南派拳術在民間流傳極廣,而且不乏黃飛鴻、方世玉、洪熙官等近代英豪的傳奇故事,香港成為功夫電影製作中心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
功夫片 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電影類型的標誌是1949年胡鵬導演、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傳》的上映。《黃飛鴻傳》不僅開創了從1949到1994年間長達77部的電影系列,其中一些基本元素更被後來的功夫電影所廣泛繼承和反覆再現:硬橋硬馬的真實武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謙虛守禮的傳統道德……但在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敘事仍然不是功夫電影的常見主題,民族情感在片中仍然處於一個非「彰顯」的階段。上一部份所論述的那種「自我東方化」的民族認同話語與功夫電影明確結合併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是從李小龍在香港拍攝的三部電影 開始的。
李小龍影片在香港的火爆,既有其自身功夫精湛和電影拍攝手法革新的因素,也有三部影片共同反映出的高昂民族主義情緒的因素,尤其是《精武門》完美地將「復仇」這個傳統武俠片的主題與民族衝突結合在了一起,陳真打破「東亞病夫」的匾額和踢飛「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牌,更成為華語電影的經典鏡頭。就影片結構來講,《精武門》的前半段——從陳真歸家參加葬禮,到忍受日本人的上門侮辱——是一個民族仇恨的積聚過程;而後半段則是仇恨的激烈釋放過程,一是陳真帶著「東亞病夫」牌匾主動上門搦戰並擊潰眾多日本空手道門徒,並發出「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的宣言,二是後來他憑著巧妙的易容術潛進日本道館,擊殺俄國大力士和日本空手道館主,正面肯定了中國人的智慧和武力,完全粉碎「東亞病夫」的侮辱,同時將全片的民族復仇情緒推到了極點,也塑造了陳真這個虛幻的螢幕 英雄形象。通觀這個敘事結構,日本空手道館作為侵略者代表的加害者形象分明,而陳真的憤怒、反抗與最終的勝利則,正是前述近代史上「東亞病夫」概念轉移和「體育強國」思想內所隱含的反抗邏輯的螢幕體現。有評論說,這部電影展現了一種「好戰的」中國特性:「永恆的、本質主義的與理想化的……絕對的民族主義者與種族主義者;強烈地反日本」。 可以說,《精武門》借用了「東亞病夫」這個的民族主義符號,套用了「復仇」這個傳統江湖故事的劇情,再樹立起日本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侵略者作為民族主義情緒發洩的「他者」,將陳真幻化成智勇雙全的中華民族的螢幕代言人,從而在取得巨大商業成功的同時也為後來的功夫電影的民族主義敘事確立了一個標準參照物。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電影中的民族認同話語表達並不是單向的,而是當時香港社會集體認同缺失的一種反映。這是「李小龍電影」流行的時代背景。由於內戰結束後兩岸對峙的局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海外華人社會普遍存在著「左」與「右」的對立,尤其是香港社會,還存在著左右兩派與港英當局的「三足鼎立」。當時的香港,一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同時,左右兩派也爭鬥不斷,港英當局採用高壓手段進行統治,政府內部腐敗嚴重。這一時期,香港的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 ,而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和台灣的「戒嚴」也令生存在意識形態夾縫中的香港和海外華人群體感到空前的壓抑和歸屬感的喪失。在現實中遭遇身份認同危機的人們轉而在虛構的影像世界尋求身份的確證,而《精武門》這部電影恰恰就為這種在現實中無處安放的民族情感提供了一個虛擬的發洩渠道。這是《精武門》成功的外部因素。
以《精武門》為代表的李小龍式的民族主義敘事僅僅是功夫電影與民族認同華語結合的一個開端。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民族主義表達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三、淡化:徐克黃飛鴻系列中包容式的民族主義敘事
徐克是80年代香港新武俠電影的領軍人物,導演的武俠電影富於想像力和創造力。而徐氏功夫電影的代表作首推他與功夫巨星李連杰合作的前三部黃飛鴻系列 。作為90年代拍攝的新黃飛鴻系列,對近代中國這個不變的時代背景,徐克一反李小龍電影中的那種華洋抽象對立的簡單世界觀,而選擇了一種更宏大的廣角鏡頭,力圖將一個清末社會全景式地呈現在觀眾眼前,徐克的世界觀因此也在另一種意義上顯得更為龐雜和矛盾:以舞獅、粵劇等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美與迷信愚昧的白蓮教的同時存在,中國人裡既有投靠洋人拐賣同胞的幫會頭目和欺行霸市的京城惡霸,也有孫文、陸浩東這樣的革命志士。影片中對清朝官員形象的處理也不是「臉譜化」的,雖然頑固不化但也有保境安民、反抗洋人的一面;同樣,影片中的洋人也並不全部是窮凶極惡的侵略者,第一部中有勇於替黃飛鴻作證洗脫罪名的神父;第三部中的俄羅斯殺手雖然狂妄地認定中國必定要遭受異國統治,但他對十三姨的感情也顯示了他尚存入性。總之,百姓、官員、洋人——徐克鏡頭下的清末中國社會,似乎每種人都有兩個面孔,這種對背景人物群像多元化的處理,使得傳統功夫片中以身體侮辱為主的「東亞病夫」的話語言說難以成為系列的主題。而且整個系列也反映出導演對國民劣根性、革命者的對外依附性、學習西方和維護傳統之間的張力等等眾多的問題的思考。這些多元價值觀的有序的摻雜不僅讓影片呈現一種萬花筒般的精彩,也讓不同觀眾能夠各取所需。徐克全景式的敘事在凸顯微觀歷史的複雜性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李小龍電影中昂揚的民族主義激情。
徐克鏡頭下的黃飛鴻是個徘徊在中西之間的矛盾混合體:黃本人是個遵守倫常的舊派人物,是功夫和中醫兩大傳統技藝的繼承者,但他的愛人十三姨卻有著留洋背景;黃在十三姨的影響下被迫接觸諸多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先進科技時,既表現出接受的一面(有時會戴墨鏡、禮帽),也有不理解的一面(對學英語、照相等表現得不耐煩),在遭受打擊時甚至也會偶爾露出排斥的一面(在寶芝林被燒燬時憤怒地命令不准再使用「洋玩意兒」)。不同於李小龍塑造的那個情緒化的、反抗的、能安慰華人失落民族認同感的陳真形象,徐克對黃飛鴻的設定讓他顯得更為富有歷史的真實感。然而在面對無法抑制的列強蠶食和現代科技對傳統的破壞時,黃飛鴻也表現出身為一介平民和一名傳統繼承者的無奈——他不是李小龍式的中華民族的暴力能力在螢幕上的代表,而是在高速現代化/西化的中國社會中仍然頑強生存著的優秀傳統文化,以及與之相伴的自強精神。
這種民族主義表達的變化,應該與90年代初香港、台灣和大陸社會經濟發展和兩岸政治空氣的緩和有著內在的聯繫。當華人所代表著的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實力差距逐漸縮小時,「東亞病夫」式民族認同話語和復仇式的民族主義情緒宣洩失去了外部市場,徐克更加包容的民族主義敘事手法,對近代屈辱史採取一種更富滄桑感的、略帶憂傷的史詩化 處理,顯得更貼合當時的社會思潮和公眾的心理需求。如果說70年代初的觀眾能夠從李小龍電影的民族主義敘事中找到確認民族認同歸屬感的激情,90年代初的觀眾則能從徐克黃飛鴻系列中喚回對民族歷史的遙遠記憶,並從包容的民族主義敘事中對純粹的「東亞病夫」式的民族認同話語進行一定的反思。
四、重構?新時代背景下功夫電影中民族主義表達的變數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大陸連續十幾年的穩定經濟發展,華人社會變得更加強大自信。功夫電影從90年代末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創作低潮後,隨著甄子丹等新老功夫演員的活躍,又重新煥發了生機。而且隨著中外交流的逐步增多,功夫電影這一傳統的華語電影類型也開始邁出走向世界的步伐,如好萊塢大片《駭客帝國》大量藉助中國功夫增強表現力,華裔導演李安拍出了《臥虎藏龍》這樣奧斯卡獲獎武俠片,還出現了大量借用中國元素的動畫片《功夫熊貓》等。這個多元化的新時代對於長期潛藏在功夫片慣用主題中的民族認同話語而言,也存在著更多的變數。
其一是個人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對民族主義敘事方式的挑戰。葉問系列是近年來最成功的對傳統功夫電影的演繹。但不同於以往的功夫電影,在劇情安排上,導演葉偉信對兩部葉問電影都採用了兩段式的結構:第一部份主要是葉問的居家生活和他與其他中國武師之間的較量,第二部份才是葉問與東洋西洋對手間的搏殺。而且,甄子丹所詮釋的葉問是個謙和、護家、愛老婆的傳統中國男子形象,武術僅僅作為他早年的興趣愛好(第一部)和中年養家餬口的工具(第二部)而存在,並不是有意識作為一種實現正義目的的工具(在陳真和黃飛鴻處均是如此)而存在的。而葉問之所以會出手挑戰東西方拳師,在第一部中,一半是不忍朋友被殺,一半是日本人的強逼下;在第二部中,也是出於對同道中人被活活打死的義憤,還有對中國武術被侮辱的不平。這裡雖然重新引入了被徐克淡化掉的「東亞病夫」概念,但螢幕英雄反抗的原因卻更加個人化了,與李小龍主動的、明顯與所受傷害不對稱的民族主義復仇不同,葉問的反抗更加被動,也更加有限度,而且其戰鬥目標也不是實現民族整體而更多的是主角個體的正義。還有個值得一提的細節:《葉問2》的後半段在描述洪震南與葉問先後同西洋拳王進行「龍捲風」搏鬥時,本來是非常傳統的復仇式民族主義敘事方式,但導演卻背離「慣例」的劇情發展,在結尾處安排了一段葉問的講話,居然把這一傳統的、復仇式的、黃種對白種的反「東亞病夫」式的勝利,扭轉為呼籲種族平等、相互尊重與理解的西式人權宣言 ,並得到了英籍觀眾的鼓掌歡呼,使之前渲染起來的民族情緒消失殆盡。這種劇情處理所體現出的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曖昧態度,折射出日前在香港社會,後殖民主義的懷舊情感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思潮。 這種個人主義的和後殖民主義的表達方式,是傳統功夫電影敘事邏輯在目前時代發展的最新形態,也對傳統的民族認同話語形成了有力的挑戰。
其二是全球化背景下與西方的再遭遇和文化誤讀的挑戰。如前所述,《駭客帝國》、《臥虎藏龍》和《功夫熊貓》是這些年來融入了中國功夫元素後取得成功的3部典型的好萊塢電影。除《臥虎藏龍》外,其餘兩部均在華語文化圈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臥虎藏龍》的票房在北美地區卻是一路高歌。探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駭客帝國》和《功夫熊貓》兩部影片僅僅是借用了中國功夫的元素作為一種推進劇情的「道具」,但劇情講述的依然是純粹美式的超級英雄科幻片和勵志卡通片,這種西方核心與東方外表的簡單拼合,在讓中國觀眾在享受西方大片的時候找到了熟悉事物的同時,也讓西方觀眾發現了能滿足他們對「東方」想像的「異國情調的(exotic)」之物,其結果自然是皆大歡喜。但對於《臥虎藏龍》這部由華裔導演李安執導的作品而言,由於李安致力於還原一個外觀上儘可能真實的清代社會(事實上他這一點做的確實比國內大多數導演要好),並用最武俠的動作演繹這個武俠故事(袁和平的武術指導),但卻在劇本上選用了一個西化的角度去詮釋夫妻、師徒、父子這幾對中國傳統倫理關係 。西方觀眾可能會簡單地走進這個充滿了「東方」式想像的武俠世界,但對於華語文化圈的觀眾而言,被完美的武俠外表所引入的卻是一場純粹西式的文化命題討論,就容易產生一種「熟悉的陌生感」,就難免會感到困惑和訴諸排斥。功夫電影的好萊塢化所反映出來的功夫元素「零碎化」和功夫內涵被替換的現象,正是西方對東方文化誤讀的結果,也是最原初意義上的「東方主義」特點。當功夫電影中的民族認同話語正面遭遇強勢的好萊塢電影對其解構和重構的挑戰時應如何做出應變,也是需要深省的。
總而言之,以洋人對華人身體侮辱為標靶的功夫電影中的傳統民族主義敘事,在半個世紀的時代變遷中不斷髮生演變,到了21世紀初,更是遭到了內部個人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話語,和外部西方主義話語的再次挑戰。同之前的民族主義敘事形態的變化一樣,現在的變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當代中國社會中人們認同觀念的變化。功夫電影中民族主義這一主題是會繼續發展、被重構還是逐漸消失,還要看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華人民族認同變化的趨勢。
參考資料:
I. 專著:
1.[英]里昂•漢特:《功夫偶像:從李小龍到〈臥虎藏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蹇河沿:《中國電影觀念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II. 論文
1.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載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
2.蔡振豐:《中國近代武士道理念的檢討》,載於《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0年12月
3.譚暢:《百年霍元甲的真實與影像》,載於《小康》,2010年12期
4.吳勻:《通俗敘事與喻象符號——〈黃飛鴻〉電影中「國家形象」的考察》,載於《當代電影》,2009年第1期
5.列孚:《徐克「黃飛鴻」系列研究》,載於《當代電影》,1997年3月
6.唐宏峰:《葉問2:民族激情的被觀看與被化解》,載於《中國報導》,2010年第6期
7.符鵬:《香港功夫電影中的民族主義書寫——以電影〈葉問〉系列為例》,載於《藝術評論》,2010年第7期
8.華靜:《文化差異、文化誤讀與誤讀的創造性價值——兼析動畫片〈花木蘭〉與〈功夫熊貓〉的中美文化差異與誤讀現象》,載於《蘭州學刊》,2010年第1期
9.傅睿純:《一次繼承與變革的武俠片試驗——評〈臥虎藏龍〉》,載於《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III.影片:
1.《精武門》,羅維,香港,1972
2.《黃飛鴻》,徐克,香港,1991
3.《黃飛鴻:男兒當自強》,徐克,香港,1992
4.《黃飛鴻:獅王爭霸》,徐克,香港,1993
5.《葉問》,葉偉信,香港,2008
6.《葉問2》,葉偉信,香港,2010
7.《駭客帝國》,安迪•沃卓斯基/拉里•沃卓斯基,美國,1999
8.《臥虎藏龍》,李安,香港/台灣/美國,2000
9.《功夫熊貓》,馬克•奧斯本/約翰•斯蒂文森,美國,2008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