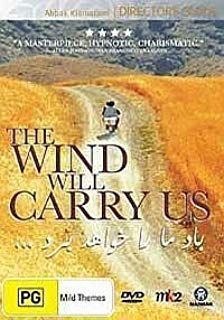随风而逝/风带着我来(台)/风再起时(港)
導演: 阿巴斯奇亞洛斯塔米編劇: 阿巴斯奇亞洛斯塔米
演員: 貝哈德.道拉尼 Noghre Asadi Noghre Asadi Roushan Karam Elmi Roushan Karam Elmi

2011-12-13 06:44:17
《電影手冊》就本片對阿巴斯的訪談(轉載)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本文譯自法國《電影手冊》雜誌1999年第12期(總第541期),梯也里•於斯、塞爾日•杜比亞納1999年9月13日採訪於巴黎,穆罕默德•哈西吉特將阿巴斯的談話從波斯文翻譯成法文。中文原載《當代電影》雜誌2000年第3期】
梯埃里•於斯、塞爾日•杜比亞納(以下簡稱「問」):在威尼斯電影節閉幕式上,您宣佈以後不再三加電影評獎。這個決定是您在獲得金棕櫚大獎之前做出的嗎?
阿巴斯(以下簡稱「阿」):我在參加上一次坎城電影節之後就產生了這個想法,只是想等待合適的機會向公眾宣佈,我覺得威尼斯電影節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人們可能認為我對那次金棕櫚獎評選感到不高興,但是我的這個決定跟金棕櫚沒有任何關係。我已經不想參加任何電影評獎。我拍電影已經30年了,也參加了30年的電影評獎,現在是該退出的時候了。以我作電影節評委的經歷,我發現很難評判知名作者的影片。應該將機會讓給年輕導演,應該努力評選作品本身而不是作者的名字。今天,人們在評獎時更注重的是作者名字……
問:擔任《隨風而去》製片人的馬爾丹•卡爾米茲告訴我們,您在開拍這部影片之前沒有劇本,您是用什麼樣的方法拍片的呢?
阿:開拍前我只寫了一個兩頁紙的提綱,把它交給了馬蘭•卡爾米茲。我已經在鄉下拍過4部影片了,在去西亞赫•達萊赫村拍攝《隨風而去》之前,我受到以前拍過片的其它村莊的影響。可是在到達萊赫村之後,我發現它跟別的村莊不一樣。在那裡,村民們改變了我的這部影片的總體構思和已經形成的主題思想。很明顯,我曾經試圖將我的觀點強加給事物,後來發現應該適應現實。
問:伊朗的電影機構是怎樣看待您的拍片方法的?
阿:這取決於兩件事。一方面,西方對我的影片的關注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儘管有關方面否認這一點。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認識到我的拍電影的方法,他們知道我拍的電影與政治無關,至少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也就讓我隨意拍了。當我用政治這個詞談論電影的時候,我想說的是我從來不用政治口號。在我們國家,有關方面尤其害怕政治口號,因為他們認為人們會受到這些口號的影響。
問:跟法國合作拍片給您帶來了什麼,比如這次跟馬爾丹•卡爾米茲合作?
阿:由於我的影片成本不高,所以並不需要國外資金。但是,合作拍片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支持,因為完成這部影片的製作後,我可以將它送到法國來,審查方面的事情就比較省心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裡的人們會在最好的條件下向評論界放映這部影片,法國的電影製作機構對待影片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善於幫助孩子成長。
問:這部影片仍然是在農村拍的,您是依據怎樣的標準選擇這個村莊的?影片中哪些部份是即興創作的?
阿:舉個例子吧。在最初的想法中,攝製組來到村子跟那位老太太商量,請求她裝作要死的樣子,我們還特意對她說是為了拍電影。但是在拍攝現場,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與她交流,因為她的確已經奄奄一息。我也無法跟那些整天忙著幹活的村民們交流,他們沒有時間回答我的問題。我從來沒見過這麼玩命幹活的,整個村子就像一個勞動集中營,甚至連孩子們也沒有時間來參加我的影片拍攝活動。我不得不放棄起初的大部份想法,交流是不可能的,況且我自己也對這個主題產生了懷疑。一方面是因為村民們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的構思問題,這部影片就像讓觀眾用拼板做一個複雜拼圖遊戲。
問:同樣真實的情況是,這是一部人們可以對現實進行多種闡釋的影片。
阿:我不信任那種只允許觀眾對現實進行一種闡釋的電影,而是喜歡提供多種闡釋現實的可能性,讓觀眾自己去選擇。我遇到過這樣一些觀眾,他們的想像力比我自己在影片裡融入的想像力更加豐富。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每一位觀眾去自由闡釋的電影,就好像這部影片是他們自己的作品。比如,有人在闡釋這部影片中的一個鏡頭時提到了西西弗斯神話,就是我們看到的一隻金龜子正在推移一個球的鏡頭,這種視點就意味著人們知道西西弗斯神話。一部影片如果能夠產生多種不同的闡釋就說明它是成功的。
問:與您的上一部影片《櫻桃的滋味》相比,人們感到《隨風而去》中的光線更加明亮,感受到了更多的對自然的愛,而且人物形象也更加豐富多彩。
阿:說到《隨風而去》,我真不知該從哪裡談起,這部影片耗費了我很多精力,尤其是錄音工作。這是我所有作品中最難拍的一部,拍攝期間我跟攝製組工作人員之間發生了很多摩擦。在觀看這部影片時,人們會感到主人公與居民之間的關係非常冷漠,這種冷漠也存在於我跟我的技術人員之間。在拍攝末期,攝製組的大部份技術人員都走掉了,只剩下我跟幾個助手,我們一起完成了《隨風而去》的拍攝任務。我的攝影指導是一位專業人員,但是他早晨不能起床,上午不能拍片,只在下午工作。拍攝工作剛剛進行了一個星期,我們就彼此明白,我們無法繼續合作下去。
問:拍攝階段持續了多長時間?
阿:九個星期。那個村子很髒,蒼蠅滿天飛,我們的許多精力和經費都花在打掃衛生、驅趕蒼蠅上了,因為蒼蠅影響錄音。我們的做法擾亂了村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使用的清潔劑毒死了不少小雞,村民們非常不高興。對他們來說,我們到那裡去不是為了工作,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電影攝製組,也沒有見過外國人到村里來。要是在伊朗的其它地區,我們是可以跟村民合作的,但是在這個村子我們無法跟村民們交流。
問:對這個村子來說電影是製造混亂的因素?
阿:是的,村民們不喜歡我們。
問:影片的主人公本身就是一個製造混亂的因素,他單獨出現在村子裡,如同一個看熱鬧的人。
阿:沒錯,村民們拒絕在攝影機前表演。在影片結尾,一些婦女從攝影機前經過,主人公給她們照相。由於她們看著攝影機,可以說主人公是「偷」拍了這些婦女的照片,這跟我們想表現的主題是吻合的。
問:請跟我們談談妻子與丈夫在咖啡館裡的那個場面,在我們的印象中,這是一場有關工作問題的爭吵,但是頗有哲學意味。
阿:這個場面中的對話是我根據自己在其它村子遇到的事情寫成的,那個女人不是這個村的村民,而是來自一座城市。人們以為那些話是她自己說的,其實這是她從書上讀到的一篇文章,但是她表演得非常好,以致人們感到那些話就像是她自己說出來的。
問:您的這部影片再次參照了大詩人歐瑪爾•海亞姆。他的詩歌具有感覺主義特徵,經常描寫死亡與毀滅。他的作品在伊朗是否擁有很多讀者?
阿:在伊朗,歐瑪爾•海亞姆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很難評論,他在全世界都很出名,有人甚至對我說他的著作發行量僅次於《聖經》。有一天在日本,我正在談論歐瑪爾•海亞姆,一位出版社的編輯一下子就找到了九個不同版本的海亞姆詩集。我在電影創作中對歐瑪爾•海亞姆的參照開始於《生活在繼續》,那是我到地震現場觀看地震災難的時候。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這樣近距離地看到過生與死的矛盾。也是在那個時刻,我感到自己很好地抓住了歐瑪爾•海亞姆的哲學思想和詩歌的靈魂。它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則:要想懂得生命,必須接近死亡,親眼目睹死亡。在地震現場,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體會,我去那裡不是為了觀看死亡,而是為了發現生命。那段日子對我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我身上也發生了一場地震——那天剛好是我50歲生日。
問:出現在您影片中的這些詩歌,伊朗觀眾理解嗎?
阿:在伊朗,詩歌是由口頭語言寫成的,也許不是現在的年輕人的口語,但它是先輩們的口語。雖然許多人都是文盲,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背誦這位或那位詩人的詩句。年輕的一代對這些詩歌知道得不多,比如我自己的孩子就對它們沒什麼興趣,他們只想看錄像。福路•法爾克赫扎德的詩歌也很有名,她是伊朗的第一位女詩人,在詩中以真誠的方式談論女性問題及男女之間的性愛關係。她在32歲就去世了,是一起車禍的受害者。她在生前就很出名,其思想非常接近海亞姆。出現在這部影片中的詩歌是她最優秀的詩篇之一,題目是《隨風而去》,這部影片的片名就來自這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早晚有一天,風兒將把我們帶走,就像一片枯葉……
問:下面這個場面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那個年輕女人(我們看不到她的臉)在擠一頭奶牛的奶,而男人卻在讀一首非常色情的詩歌。他們每個人都在向對方奉獻一份禮物:女人給男人提供奶,而男人則給女人讀詩歌。可以說這是一個真正的描寫愛情的場面。
阿:這是您的闡釋,但是非常優美。還有人對我說,男人要去找奶,奶代表著黑夜中的光明。這份禮物(奶或者白色的光明),女人將之送給了未婚夫或者丈夫,即那個在地下挖東西的男人。對我來說,非常有意思的是看到她和未婚夫在黑暗中工作,並且以地下的方式進行交流。
問:可是那個地下的男人在幹什麼呢?
阿:他說自己正在挖一個坑以便安置天線,為了進行交流。
問:交流是您的這部影片的主題之一。影片的主人公只能在一個有限的地方通過手機接收到外界資訊,這地方就是村子的墓地。
阿:您的這個解釋非常好,所有村子的墓地都在山丘上,我經常打聽這是什麼原因,可是沒有人能回答我。
問:處在生命與死亡的游移不定之間,電影的地位是什麼?是為了拍攝死亡嗎?或者是為了誕生新的生命嗎?
阿:實話實說,關於這個問題我什麼也不知道。總之,電影是為了記錄事物的。當人們沒有記錄下某件事物時,人們就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這是跟畫面的威力相聯繫的,畫面具有比現實自身更加強烈的資料性。
問:在《生命在繼續》中,人們被帶到一個在地震央遭到毀滅的村莊,亡靈在廢墟上空徘徊。在《櫻桃的滋味》中,死亡再度成為影片的主題,這部影片中也有對葬禮儀式的描寫。您的影片表現的主題好像多少都跟死亡有關。
阿:這也許是無意識的。拍攝《生命在繼續》的經歷尤其使我感到人生如戲,比如我遇到過這樣一個場面,一些村民正在洗孩子的裹屍布,與此同時他們也在洗桌布。這部影片捕捉到的東西更多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由於地震帶來的災難,人們當然感到悲傷,但是在他們內心深處,他們為自己能夠繼續生存感到高興。海亞姆的詩歌或哲學很好地解釋了這種人生如過客的思想。有人說世界上最悲哀的音樂是鐘錶的「滴答」聲,它使我們想起飛逝的時光,想起自己在不斷地接近死亡。表面看來這些「滴答」聲沒有什麼區別,但事實上每一聲都與前一聲有不同,因為後一聲總是比前一聲使我們更接近死亡。如果人們過份注意這種事情,那就只有去死的份了。但是,有些時候人們依然會注意到死亡的存在,比如發生地震的時候。在我們為死者披麻帶孝表示哀悼的同時,我們每個人心裡也都體驗著某種快樂,僅僅因為我們自己還活著,我每次離開葬禮現場時都有飢餓的感覺。去年,我參加一位電影家的葬禮,女人們站在一邊,男人們站在另一邊,這位電影家的夫人全身穿著黑,顯得更加漂亮。站在我身旁的一個人對我說:「看他妻子多漂亮!」即使在這樣一個有關死亡的具體情境中,這種心情也是真實的。
問:您對自己的影片有偏愛嗎?
阿:有吧,比如說我比較喜歡《特寫》,其他片子一般(笑)。
問:您跟《特寫》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嗎?
阿:我在拍攝這部影片時沒有時間思考這個問題。其實,拍《特寫》之前我正在籌拍另一部片子,只是到了最後時刻才臨時改變主意,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跟攝製組一起拍了這部片子,拍攝階段持續了40多天,我白天拍片晚上記拍攝日記,經過剪輯合成後就被送到德黑蘭電影節放映了。通常情況下我無法跟觀眾一起看自己的影片,但是有兩次例外,一次是在坎城看《櫻桃的滋味》,最近一次是在威尼斯看《隨風而去》。通常情況下我是不看自己的片子的,但是我跟觀眾一起看了《特寫》,為了證實影片中的一切是否被安排得很好,我從頭看到尾,好像剛剛發現這部片子一樣。我在看自己的其它影片時,哪怕有一位觀眾離開影院我都能知道,但是看《特寫》時不一樣,因為主人公的故事一直吸引著我,直到最後我的視線都沒有離開螢幕。與我的其它影片相比,這部影片最不造作,我像所有觀眾一樣非常喜歡它。
問:在《隨風而去》中有沒有您自己的影子?
阿:有的,但主要不是通過主人公表現出來的,我從影片中的那個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樣,在《特寫》中,我通過阿里•薩巴齊安這個人物和阿漢卡赫的家庭認出了自己,這個人物被認為從事詐騙活動,我既像那個騙人的主人公,也像被他欺騙的人。在所有這些影片中,有些人物確實像影片的導演。在《隨風而去》這部影片裡,咖啡館的女人像我,只不過她是女人而已。
問:您的電影越拍越像謎。
阿:拍電影就像治病,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治療方法(笑)。人們可以通過影片發現電影藝術家的人格,但是影片又不必非得跟它的導演完全一樣,因為導演隱藏在他創造的人物背後。
問:在伊朗文化中,無意識佔有一定的地位嗎?
阿:在伊斯蘭教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應該注意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意識並不佔據特別的地位。弗洛伊德為我們開脫了所有責任,比如將責任推給父親。伊斯蘭教中沒有這樣的父親形象,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在當代的伊朗,心理分析也在發展。在藝術領域,無意識具有重要地位,比如您剛才談到的電影與死亡之間的關係就跟我的無意識有關。
問:在您的大多數影片中,兒童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隨風而去》中,您是怎樣處理兒童與成人之間的關係的呢?
阿:我跟協會的距離疏遠了,也就是我為之工作過的伊朗青少年教育發展協會。我跟自己的孩子們也疏遠了,他們已經長大成人。雖然我跟他們的關係疏遠了,但是兒童的生活觀繼續吸引著我的興趣。這種觀念既狡黠又神秘,接近於伊朗神話的觀念,特別是海亞姆的觀念:現實生活中的兒童想像著另外一個世界,他們對日常生活抱有很好的態度。他們在感情方面不欺詐,喜怒哀樂毫不掩飾,打歸打罵歸罵,相互之間沒有仇恨。他們建設,然後很快就破壞自己所建設的東西。他們對生活的理解比我們好,無論如何比我的攝影指導好,他每天要睡到下午兩點(笑)。
問:在這部影片中,孩子不是在教育成人的嗎?
阿:在影片中的某個時刻,孩子說他希望在考試中取得成功,也希望老婦人恢復健康。我喜歡讓這個孩子反抗成人,拒絕跟成人和解。孩子保持著自己的人格,保持著與成人之間的距離。
問:這個村莊的結構像一座金字塔,孩子為成人作嚮導。
阿:在《生活在繼續》中也是這樣,孩子擔任著嚮導的角色。我認為孩子的生活觀念比我們好,儘管我們的閱歷比他們多。如果注意觀察,你就會發現他們向我們展示的是生活的本來面目。他們沒有死亡的思想,他們知道人先是活著,然後就消失了。
問:演員的行為方式跟孩子(比如這部影片中的那個孩子)有關係嗎?人們能夠跟他有什麼樣的協約呢?
阿:應該跟他一起玩(表演),否則他就不表演,也就是說你自己要成為孩子。孩子不考慮金錢或工資問題,沒有合同概念,也不考慮什麼名譽問題。如果我們自己不去想這些東西,就有可能把工作做好,我嫉妒孩子們。
問:這部影片中有一個大人將烏龜翻過來,讓它背朝地,這是個孩子般的行為,有些殘酷。
阿:這個行為確實有些孩子氣,但是烏龜自己又將身體翻了過來,生命在繼續。
問:與您以前的影片相比,這部影片的錄音多了一些人為的東西,後期錄音工作是怎樣進行的?
阿:聲音跟畫面一樣重要。觀眾可以通過聲音聯想到一些事情,就像通過畫面那樣。這部影片中的好幾個人物都沒有在畫面中露面,但是人們可以通過聲音感覺到他們的存在。在拍攝《哪裡是我朋友家》時,我讀過一本譯成伊朗文的關於布萊松的書。有兩位電影藝術家人們不能不關注,第一位就是布萊松,尤其是他的聲音觀念。投射到螢幕上的畫面只是立方體的一部份,是一個平面,而生活是多面的,聲音產生了空間的立體感。通常,人們拍片時總是傾向於堵住現實中的聲音。其實,是聲音使影片產生了立體感,不僅要錄製鏡頭內部的聲音,還必須補充畫外的聲音,使影片產生真正的立體感。
問:這些人物沒有出現在螢幕上,但是人們能聽到他們說話,我在想您是否喜歡幻影。
阿:是的,他們就像幻影,比如那個用馬達製造聲音的人。我們曾經對十多個人做過聲音實驗。那個人們看不見的人應該給人以隨時都會闖入這個空間的印象。馬蘭•卡爾米茲跟我講過他在布萊松的一部影片裡演過的一個角色,他只有一句台詞,而且是畫外音:「他來啦!」就這麼一句話他好像重複了十幾遍,以便達到布萊松所要求的語調(這裡是指影片《巴爾塔扎爾的奇遇[Au hasard Balthazar]》——採訪者注)。我再給您舉一個有關聲音的例子:這部影片中有這樣一個時刻,那個人們看不見的男人正在挖東西,但是人們聽到了他挖東西時的聲音,同時還聽到了一隻鳥的聲音,拍攝現場並沒有鳥,鳥聲是在其它地方錄下來的,我在後期錄音時加到了聲帶中,為的是更好地表現環境。
問:按照您的看法,我們幾乎可以說聲帶講述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阿:正是這樣。我們可以有五條聲道,以便使畫面產生另外一個維度。影片中有這樣一個場面:為了告訴村民們那個挖東西的男人被埋在了瓦礫下,主人公駕駛汽車沿著山坡朝村子急速開去。為了使這個場面更有戲劇性,我在汽車的聲音之外加上了其它聲音,我使用的是聲音而不是音樂。
問:所以您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即聲音不是現實主義的,相反,它可以使影片產生一個非真實的或超現實的維度。
阿:是的,只是別太歪曲現實。這是一種接近現實的聲音,同時又是經過加工的。
問:在觀看您的影片時,人們是否可以理解或感受到伊朗的現狀?
阿:不可以,兩者之間沒有直接關係。這也是我應該向自己提出的問題。生活在伊朗,我受到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的影響。我是伊朗公民,我的護照是政府發了,但我不想讓我的影片也有伊朗護照。在伊朗,人們譴責我是為外國電影節拍片的,認為我是錯誤的。我是為人類拍電影的,我的影片沒有精確的地理界限,它是關於整個人類的。電影沒有護照,就像樹木一樣。
問:這是否意味著您可能在伊朗之外拍片?
阿:我是伊朗人,就像影片中的村莊是伊朗的村莊。我是在伊朗文化哺育下成長的。我有在這裡拍電影的可能,但是如同足球隊員一樣,在主場作戰可能會把球踢得更好。足球的規則是國際性的,所有國家的足球都是圓的,人們沒有必要懂得所在國的語言,但是在自己國家的足球場上踢球會踢得更好一些。
問:在自己國家踢球同樣會有觀眾,您在伊朗有觀眾嗎?
阿:我在這裡的觀眾更多。以前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笑)。
問:您沒有提到其他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電影家的名字。
阿:比如,塔爾科夫斯基。他製作影像的手法非常豐富,既是現實主義的也是超現實主義的。對我來說,他不是一位俄羅斯電影藝術家,而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來自一個被人們稱做「電影」的世界。
問:在您的這部非常特別的影片中,現實的東西跟抽象的東西混合在了一起。這改變了人們對您的電影的看法,您以前的電影可是與現實緊密交織在一起的。
阿:接近夢想的電影更美。我不知道您將把我歸為哪一類(笑)。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