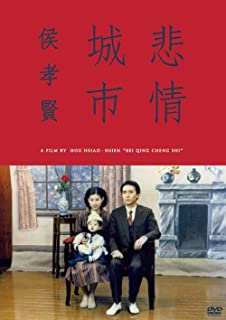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1-03-30 21:28:35
日頭出來滿天紅——台灣歷史記憶中的身份認同
「思想起,日頭出來滿天紅,枋寮過去是楓港,希望阿哥來痛疼,痛疼小妹做工人。」
《思想起》早在清代就風行於南台灣恆春鎮一帶,台灣大約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會哼唱此曲,民國六十年代陳達老人抱著貼著膠布的老月琴歌喉瘖啞地再度將這支親切而質樸的民謠改編並傳唱開來。這是自兩廣、福建渡海東來的先民在墾拓南台灣的蠻荒之地時,因思念故土、難忘戀人而表露的綿綿情意,真摯的旋律和歌聲每每聽到便覺繞樑三日。
然而,在這純樸的民謠中借自然物作為比興脫口而出的詩句——「日頭出來滿天紅」——竟成了台灣電影《悲情城市》中險些害死一位里長的罪魁禍首。在慶祝台灣光復而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日子裡,這位對「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講究完全不知情的里長,依照他熟悉的自然現象和民謠歌詞,將國旗錯誤地反掛,差點招致死罪。
《悲》中的這則情節實則蘊含了深刻的寓意。「國旗與國歌等國家的象徵物可說是將『國家』這個永遠不可及的符旨,取得一種本質與本源假像的重要替代品。顯示台灣與中國所謂『血濃於水』的國家關係不過是語言所建構的神話,由法律的暴力來加以維持的」 (林文淇,1995)。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作為掌握政權的少數外省人,在剛剛脫離日本政府51年統治的台灣發動了「二二八」事件,飽經戰亂而敏感脆弱的台灣及人民再次遭到來自「外人」殘忍的清洗和鎮壓。這場悲劇早已成了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像徵,並可以說是二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在台灣身份的認同的嬗變過程上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在「二二八」死亡陰影及後續長達38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很多台灣本省人都對此事件隱諱不談;甚至在多年以來,此事一度被台灣官方歷史消去,這種暴力的禁聲如同國內歷史對於「大饑荒」真實原因的避而不談,對人民的污衊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也正是在這場慘劇之後,「少數本省籍菁英則以族群身份認同為依託進行鬥爭,隨著台灣政治轉型和政治參與的擴大,本省籍菁英的自主意識不斷強化並得到了部份本省人的支持,以省籍區隔為背景的『台灣(本省)人主體意識』不斷髮展起來」(陳星,相靖,2009)。在這一點上,我贊同王曉明在《新的國家認同及其未來》中的觀點,在政府獨大的背景和支配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實踐下,在現實的黑暗中四面摸索,成了共同體里民族同胞的共同命運。與此同時,我從馬世芳在台灣音樂歷史的記憶中得知一個我想不通的差距:二戰之後的島內和大陸, 同時受到兩黨的集權統治,結果卻大相逕庭,一方的人民在激烈的抗爭下逐漸開始了台灣社會身份認同的重新建構,另一方的人民則絕大多數在絕對意義下的服從中作為社會國家的政治子民,無條件的付出盲目的政治熱情與忠誠。對於這點,我只能謹慎的猜測,是否因為腦內在日本殖民時期獲得了民主政治、自由意識的長足發展,多少打破了普通老百姓蒙昧的認同狀態,而不像大陸的人民在高壓下仍舊積極投身於無意識的政治。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派系鬥爭日趨激烈,「台灣的民眾身處於類似『大風吹』的換位競爭中,社會以及反應社會的電影,出現了很多奇異複雜的認同游移現象(盧非易,1998)」。而2008年上映的《海角七號》竟在十多年後印證了這類似政治背景下的認同游移現象。《海》作為一部鄉土氣息極其濃郁的台灣本土電影,將60年前的前殖民時代與後殖民時代時空對接,並有意無意地選址民謠《思想起》的發源地恆春小鎮,其中刻意營造的與日本曖昧複雜的情愫,宛若一封台灣寫給日本的情書。如同《悲》中光復台灣的場面,被勾畫成國民黨士兵持槍阻隔了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令台灣人唏噓不已,這份寄了60多年的情書終於在台灣人眼下物歸原主。而《海》中對日本形象的書寫,「需要放置於台灣特殊的社會語境與氛圍中進行把握」(劉翠霞,2009)。
時至今日,台灣本省人多數仍對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外省人充滿敵意,儘管這敵意可能因為共同寄居在一座島嶼上萌發出的同鄉情懷而有所淡化。台灣身份認同的重新建構已經以「主體意識」的形式加以鞏固,這「是台灣文化思潮激盪的結果 ,也是近些年來政治生態演進的必然」(郭亮亮,段鳴鳴,2010)。在看《悲》時,我在思考,中國還有可能收復台灣嗎?是否中國「母親」和她的人民習慣以大陸自居,收復台灣的心太過於自大了?在這百年的分隔間,台灣的心是不是早就寒了?換做我,我也只好像澳門那樣說聲,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
從兩岸歷史觀、價值觀上的差異和隔膜,台灣身份認同的游移和鞏固角度來看,讓人不由得思考,倘若尚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抱有統一的希望,那麼究竟是應該仰仗有識之士的推動,還是依賴兩岸教育體制下的學生的宣揚呢?我認為這兩者很難截然二分。有識之士是從學生慢慢成長起來的,而今天的教育體制下的學生又可能成為明天的有識之士。所以,關鍵也許在於,無論是有識之士還是學生,是被動地接受現有的民族國家的想像,還是積極主動地去承擔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批判來重新展開新的國家想像這一任務。或者說,現有的社會體制——無論是教育制度、學術機構的各種組織方式,還是媒體的組織方式,是否允許人們去積極承擔這一任務,還是只是要求人們被動地接受既有的國家的想像方式。此外,一個國家的民族想像也不是只有一種,而是有好幾種,每個團體或成員在其中都會發揮各自的作用。比如,具體到既有的主流媒體中的民族國家的想像里,那麼作為政府的智囊團之類的有識之士或者媒體從業者,在其中就會發揮很大的作用。而對於尚未定型的未來的想像,那麼學生或者和政權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密的知識者,則會發揮更多的作用。
最後,如真若王曉明所說:「第三世界人民的社會或集體認同,通常是從對第一世界的抵抗中獲得動力」,也許一場不被期待的全球範圍內的危機反而能促成台灣與中國的「破鏡重圓」。當然這種不負責任的推測只是我一廂情願的胡思亂想,或然囿於意識形態、國家利益、身份認同等的差異,台灣在我們可預見的未來里無法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但仍願在這片東方的土地上的天天月月,日頭出來滿天紅。
參考文獻
[1]陳星,相靖,「台灣主體意識」的概念性解析,台灣研究集刊,2009年(04)
[2]郭亮亮,段鳴鳴,《海角七號》:台灣身份的認同和確認,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02)
[3]林文淇,「回歸」、「祖國」、「二二八」:《悲情城市》中的台灣歷史與國家屬性,當代,1995年(02)
[4]劉翠霞,從殖民記憶到後殖民想像——台灣電影中的「日本書寫」,社會科學,2009年(11)
[5]盧非易,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台灣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