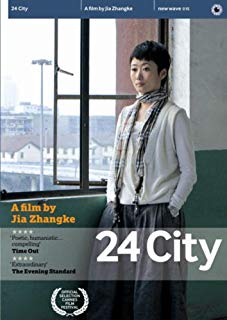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4-22 06:52:49
小賈的敘事實驗?
關於一種不可能的視角:《24城記》的一個標誌性鏡頭就是俯拍廠門,穿著灰色制服的人們一起湧入,請問什麼樣的人才能看到這樣的場景?你只能置身人流之中進行想像。還有大合唱時從指揮的角度看到的場景,但觀眾無比清醒地認識到自己不是指揮。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處在這種位置就決定了移情的困難。觀看這個電影就是在這樣一種尷尬的位置上搖擺不停。這是置身任何一種敘事都覺得不對勁的尷尬,在後面賈樟柯將這種尷尬發揮到了極致,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尷尬並沒有被浪漫化為一種迷霧,而是堅絕地不避諱各種無聊、無奈、抒情的力有不逮,在這樣破綻重重的敘述面前我們也只能平靜以對。
然後,第一個戲劇性橋段來了,大會的聲音虛化,大會作為背景虛化,我們都等待故事和主角出場,這個工人沒有出席大會,後來知道他三軍了。這個人被凸顯出來,這是從集體場面到個人史的迅速跳躍,如果說前面的集體場面是那樣的缺乏立場搖擺不定(沒能構成日常的機械操作場景和沒能構成歷史性的交接大會),這裡同樣是無力的個人視角,一陣絃樂好像要推出一個悲慘苦情故事,但是什麼都沒有,僅有一個空白的、好像窗戶上印出的影子般重疊的影子一樣的位置,既是欲說還休,又顯示了一種隔絕,集體大型事件與一個憂傷的個體的隔絕,兩者都不能成立,那就淡入、淡出吧。。。這種手法後面也會看到。賈樟柯用了一種類似MTV裡的靜止人物肖像,在那些主旋律或歌頌人間真愛感嘆世態的歌曲中頻頻出現,通過背景的抽離和人物面部表情的捕捉,我們彷彿看見這張臉就是喜怒哀樂本身,所以這種手法用以表現某種普適的情緒或「人性」再適合不過。對了,就是人性。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片子裡,「人性」多次挾著煽情的音樂閃現。這是賈同志試圖製造的另一個錯位。把MTV置換到紀錄片裡,觀眾就會覺得即使短暫的特寫也長的不能忍受,因為這樣的情緒跳躍太陌生。片中的真人凝視鏡頭、凝視我們,造就了一個虛化的張力時間,我們馬上要問這樣長時間的凝視是何故啊,我們彷彿是某種被凝視的存在,但我們是誰?是拍攝者還是講述者還是什麼人?好像更像一個虛空的位置。就像後面的假口述史,同樣不明確那些人的講述指向何人。
當然,悖論的極致就是假口述史了。賈的假口述史讓觀眾陷入一種勞務,一種額外的勞務,進入配合導演編織一種紀錄片敘事的勞神費思的過程,迫使觀眾在敘事建構中扮演一種積極的角色,觀眾會時時想僭越編劇的位置。如果要把檔案故事化作口述,可以由當事人口述,可以由相關人口述,可以由導演口述,賈恰恰找來了最不相幹的人,擺到了口述者的位子上,說一些別人嘴裡說出來的話,然而那些嘴的一張一合、那些聲情並茂確是演員本人無疑,這樣的表演被無限放大,簡直是一開始就阻斷了移情可能的絕望的表演,被眼睜睜觀看著,這種表演的一切努力和痕跡盡收眼底,洩漏了演員心目中的尺度、甚至電影的尺度。如果說導演是知情人,觀眾也是知情人,演員恰恰成了局外人,歷史怎樣進入當事人的個體生命、怎樣進入演員的個體生命成了一個悖論的難題。演員們動用一切力量接近當事人的日常和被拍攝的日常,卻完完全全地失掉了這種日常,日常變成了普適話語於是煙消雲散。真正的個體性在此不復存在,只有講著宏大話語的假人,故事從嘴唇里流淌出來,表演富有層次,但他們的形像是隨時會隱沒的,留下的只是位置,只是淡入和淡出。如果口述史是這樣編織的,那真是莫大的諷刺。
從呂麗萍舉著吊瓶走出樓的第一個鏡頭,我們就急迫地尋找著這個影子和一個真的女工「大麗」的影子的疊合,之前的幾個鏡頭中,導演先是描摹了一下整個工人宿舍區的情況,小路口上有幾個「閒散人等」朝鏡頭看過來,確定無疑地提醒真實性和介入的姿態(回想賈樟柯以前電影對攝影機位置的迴避),然後給了坐在二樓樓梯上對著街上織毛衣的紅衣女人一個特寫,她也屬於前面的真實,直到呂麗萍出現,她從樓上看見問道:「大麗出去啊?」這一聲喚出了演員的出場和整個虛構口述的出場,樓上的她和樓下的呂麗萍奇妙地相遇了,紅衣女人就像一個啟動的機關,這個對「單位」的事情一定熟悉於胸默默關注的女人,以此種方式默許了虛構的介入。當陽光從一排排乾枯樹枝掠過的時候,呂麗萍講述的聲音開始了,這時似乎我們的確不必追究她的身份了。賈樟柯多處陳列舊物,但卻無意拼湊一個舊場景,我們甚至無法通過這些物件想像一個舊時代,它們是少量的、稀少的,既煞有介事的擺出來,又缺乏重量和歷史感。先後有老侯年輕時的工作證、文化站的規章、大麗的菜票等等泛黃證物,越發提醒著一種文本性質,無法指向歷史的證物和無法還原的歷史場景,只有片段言辭+編造的破碎文本,一個時代的輪廓越發模糊不清。
汽笛、軍號、軍事片、揪心音樂又響起,配合歐陽江河的詩,片中最詩意的地方就是對車間舊物、舊機械和勞動場景的呈現。每一個人的口述後牽出一個歷史記憶,汽笛、《血疑》、《小花》,再跟現實場景交疊,然後開始是新的電子音樂,然後是齊秦《外面的世界》,然後是拆除機器後的廢墟,讓我想到M50附近的未被資本收編為loft的廠房,開滿油菜花的地裡也有人在擺拍,24城樓盤背景-開車女人-油菜花田-擺拍女人-經過農婦,構成一幅超現實畫面,她是去懷舊的,去看母校廢棄的教室,趙濤的講述中天黑下來,又一天在熊貓電視塔上,俯瞰積木森林。
賈樟柯不僅讓演員來口述,還擺拍普通人靜態肖像,給文化站平常的打麻將場景配上揪心音樂,然後看到一個倒水的服務人員站立在鏡頭前略顯不安的一刻,還有夫妻倆相擁站立和女人單獨靜靜站在陽台上窗外夜幕前的寂寥效果,車前吹風機前面的胖女孩,兩個表情純真的男工人,拆遷現場的眾人合影,都看鏡頭,都是擺拍,期間眼神遊移,呈現出強制抒情的處處脫節。按照觀影常識,這樣的抒情應該出現在鋪陳的喜劇性之後,這裡的抒情是飛來的,是抽離背景的,我們就歸為莫名心悸吧,這樣不僅演員不知情,就連當事人都是不知情的了,那麼你說時代變遷、集體記憶的悲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部電影越看到後來,越感覺情感表達的收放自如,表現為不動聲色的節奏,時光變換,導演無意記錄真實,索性拼貼。在某些時候,可以感覺到賈不是在製造電影而是想製造繪畫,把真人置入肖像畫的衝動,陳列場景的衝動,所以我們可以長久地凝視那些劇照,比如「成發集團」四個大字拆下來的場景、油菜花田的場景,或者每個每個演員口述者的定格也夠虛擬,這時配樂、配音不重要,另一重的聲音、影像(《血疑》《小花》)完全可以是抽離的,可以是強制抒情,也可以是強制抒情的反面,無所謂。 舉報
評論